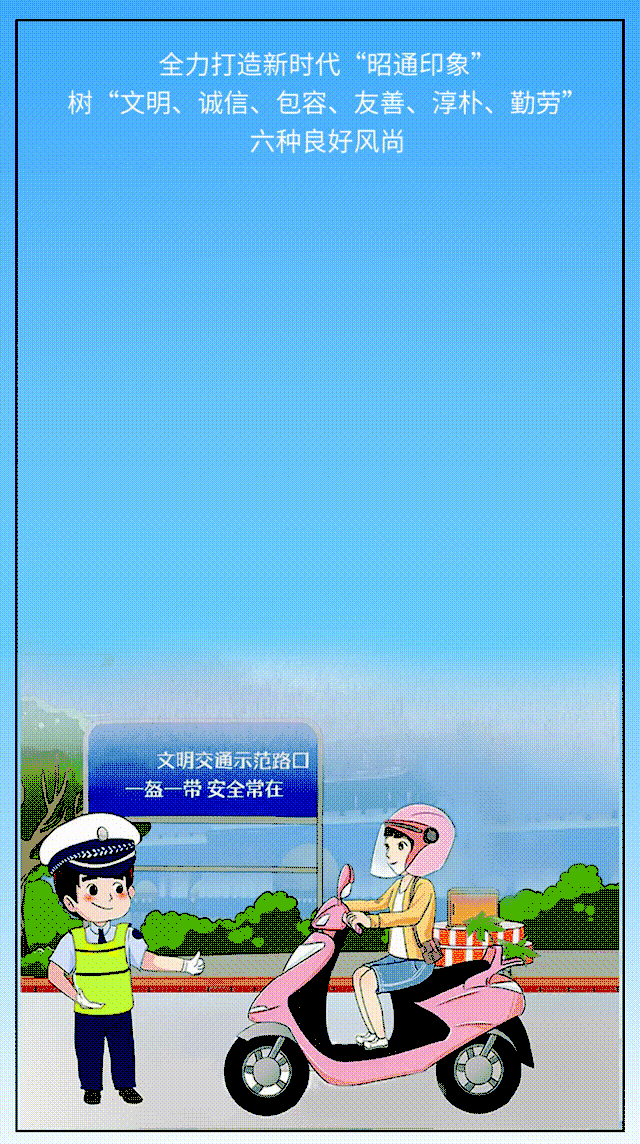2024-10-22 15:31 来源:昭通日报



开栏语
当前,我们正处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无数平凡英雄拼搏奋斗,汇聚成新时代中国昂扬奋进的洪流。今年,正值新中国成立75周年,昭通市融媒体中心特别推出《在梦想的交汇处》访谈栏目,充分挖掘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推进昭通高质量跨越式发展过程中各个行业涌现出的有梦想、敢担当、善作为的奋斗身影。通过与他们深层次的对话,记录他们在推动行业发展、社会进步过程中的经历、思考和奉献。即日起,在《昭通日报》版面上陆续刊发《在梦想的交汇处》系列报道,以飨读者。
2021年5月21日,《小说选刊》杂志社、云南省作家协会和镇雄县委宣传部共同在京召开长篇小说《回乡时代》研讨会。与会研讨人员认为,《回乡时代》的“反乡愁书写”将成为中国乡土文学的重要写作方向,诗和远方都是脚下的故乡。
作为研讨会协办方,镇雄县委宣传部是《回乡时代》的作者尹马的供职单位。从14岁开始写诗的尹马,并没有像他的作品一样走出云南东北部这个叫镇雄的县城。如果沿着出走的路再往回走,老家“庙坎”对他既是一种召唤,也是他理解的乡村世界的模样——很多人从这个地方走出去,走到向往的远方,然后,再走回来。
在文学圈子里,很多人都知道尹马写诗,但其实他也写小说、散文,甚至作词。在出版长篇小说《回乡时代》之前,尹马于2011年出版了小说集《蓝波旺》,接着又是《天坑》,并陆陆续续在国内刊物发表约30篇中短篇小说。

尹马参加云南省作家协会“大道昭通”采风活动时在威信湾子苗寨的留影。(受访者供图)
1977年出生的尹马,17岁就开始扬名,那一年是1994年。到2021年的《回乡时代》研讨会,27年时间,没有一件作品不让他满意。诗歌是什么?小说是什么?散文是什么?文学体裁似乎不重要,关键是文学作品所承载的内容,以及内容的表达方式。作为离语言最近的诗歌,尹马小说和散文中诗化的语言、故事化的叙述,往往让读者不愿跳过每一个字词。
如果说诗歌是世俗洪流中的一条安静支流,那么,小说和散文则是其中的泥沙,注定要呈现洪流的本来面目。
“反乡愁书写”似乎是《回乡时代》研讨会首次提出的概念,时至今日,3年多时间里,尹马在与诗人王单单的一次对话中作出注解:每一个离开故乡的人,都会把自己想象成从故乡射出去的一枚箭矢,他们的乡愁驱使指向的是“回得来”,当所有“距离”在慢慢消解成为各种“速度”,回乡不再是一个事件,而是一种满怀期待、有着温暖牵引力的必然。
但实际上,像回旋镖一样的乡村人物,回乡的很大缘由并非乡愁驱使,而是乡建牵引,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成乡村振兴这一政策的召唤。
那么,人们从事文学创作到底需要干什么?
“我在这里生活,肯定避不开种种‘镇雄现实’的撞击,逃不掉一个写作者的责任与良知。我会一直写我的‘乡下’,写我身边的每一个亲人。”一段时期,周末或者节假日,尹马会坐上从镇雄县城通往庙坎的绿皮乡村客运车“返乡”。在狭窄拥挤的车厢里,他会与同样去往“庙坎”或中途下车的乘客聊天,这成为他观察乡村世界的一道窗口,那些没有经历过的人生,就此徐徐展开,作者与作品人物的相遇,是最温暖的时刻。
尹马的文学作品没能提供观点,却与读者分享了情绪价值。从他作品的主人公身上,能够看到感性、乐观、悲悯、不屈的性格,当以故事化的方式展开时,顺利地获得了读者的认同。
《从我手中接烟的人》是尹马新近完成的散文,在村口路上行走着的形单影只的老年人、因各种原因返回庙坎的中年人、年关回家穿着时髦留着卷发的年轻人,尹马的笔让人理解民间哲学里的乐观,一种妥协于现实的乐观,是无论如何也要好好活下去的乐观。
“你没有感知或者经历过的东西,文学会给你。”对文学寄予厚望,但这种厚望又往往被现实击碎,“有多少人能看到你写的东西?”在信息碎片化尤其是短视频成为传播主流的当下,每一个深度写作者难免会自问。
文学不能解决什么问题,但它能提供看见世界的窗口,对已知的世界心怀感激,对未知的世界充满好奇。
2024年9月23日下午,笔者本想造访多次出现在尹马作品中的庙坎,但尹马说:“我们去王家沟吧,那里干净、纯粹。”
距镇雄县城约20公里的王家沟,是一个独具特色的峡谷村落,清澈的河流两岸,数十家民房稀疏分布,民房的边沿是陡峭的岩壁,岩壁的另外一端就是镇雄县城方向。

王家沟航拍。 实习记者 兰波 摄
初秋的阳光和微风弥漫在王家沟,在王家沟的河流之侧,我们与尹马完成了一次以笔下与乡下为内容的对话。
诗歌里的村庄
是一个邮票大的地方
记者:王家沟的确很美,你所说的“干净、纯粹”,怎么理解?
尹马:这是我理解的乡村世界应有的样子,也是我要表达的乡村世界的样子。
像我这样的写作者,虽然吃住在县城里,但生活仍在“乡下”,从来没有离开过故乡。我一直都在写故乡,因为我们的故乡是回不去的,但这些年我们很荣幸看到了故乡的复苏。
记者:你第一次写诗是什么时候,这首诗是怎么产生的?
尹马:我是一个对文体意识比较模糊的人,我甚至无法定义我的某篇作品是小说还是散文。我第一次写诗是在读师范学校一年级的时候,我写了一篇名叫《小桥流水》的散文诗,在一次全校作文展览上,我的语文老师写了8个字的评语:文采飞扬,韵味无穷。我还记得描写的就是我的家乡的木桶沟,它属于赤水河的支流,我经常在我的作品中提到木桶沟这3个字,木桶沟是一个地名,但是那条河也称为木桶沟,它流经我家庙坎,我最早的散文诗写的就是这个地方。那时候我主要写故乡、田园风光等题材。
记者:第一次的写作就和家乡联系起来了?
尹马:对,就是写我所居住的小村庄里的那条小河,河上边的那座小桥。为什么刚才我要补充我的文体意识是有点模糊的,因为那时候我没有刻意地分行,我想写多长的句子就写多长的句子,想写多短的句子就写多短的句子。这篇散文诗大概就是300多字。
记者:那是一个对诗歌极度狂热的时代,镇雄作为一个祖国西南的边远小城,当时的诗歌创作处于什么状态?
尹马:在我开始写诗之前,镇雄就有一个叫余夫的诗人,在全国都有点名气,他在《诗刊》上发表了作品。和我一起写作,写出名气的就有郎启波、王军、陈传雄、冬末等人。
那个时代,诗人是自带光环的,如果说你会写诗,大家都会认为你很了不起。像北岛他们那一代人,无论走到哪个地方,只要有诗人在,都可以混口饭吃。
那时候我经常在《语文报》发表作品。《语文报》主要是针对高中生的版面,我曾经在文学版面整版若干次发表了诗歌。那个时候,《中学生文萃》等杂志每年都会联合评选中国十大校园诗人。1996年,我就被评为中国十大校园诗人之一。
那时候的文学是至高无上的,它是一种光环,你会写文章,你就是一个很有出息的人,会受到社会的尊重。
记者:在诗歌的写作中,哪一首诗能够代表你写作的最高水平?
尹马:这个选择对我来说很纠结,我觉得我发表过的诗歌,每一首我都很满意,不满意的都是没有发表的。如果非要选一首的话,那就是《落日浑圆》。这首诗在2019年发表在《诗刊》上后,被翻译成其他国家的语言发表在海外杂志上,这首诗的影响相对来说要大一些,但我觉得我自己满意的不止一首诗。
落日浑圆
三十年前在深山,落日浑圆
我喊自己的名字
为自己壮胆。林间的兽,只认识我的父亲
它们,借一片树叶取笑我
借一捧月光追赶我
落日浑圆,落成我的偏头痛
三十年后我打着父亲的旗号
在城市的丛林里,小心翼翼地做一个
父亲。我那么孤独
没有一片树叶,像深山里的树叶
那么锋利。落日浑圆,一爿月光
像一个贫穷的女人
不敢提及被我爱过
记者:这首仅有13行的诗歌,写到了深山、落日、父亲、爱情……这些是你平时写乡下表达的一些意象吗?目前这首诗歌传播很广,你站在你自己的角度评价一下,这首诗歌为什么会取得这样一个传播效果?
尹马:我对意象生成执迷不悟,我不去直接叙述我的感受,而是通过30年前和30年后,对落日、城市、森林以及我的经历进行对比。30年前,我在故乡的丛林里游荡,和我父亲一起。30年后,我同样是在深山,只不过是在城市的丛林里面小心翼翼地做着一个父亲。这是在写一种生存的境遇,我可能在语言的跳跃性上、对语言的生成上遵从了古典诗歌的意象概念,但它的意境是一个村庄的变化。
福克纳曾说过一句话:“我的一生都在写一个邮票大的地方。”对我来说,这个邮票大的地方就是我的故乡,像王家沟、木桶沟、庙坎这样的地方。
乡村题材作品应该是“乡音”
才能够直接抵达读者
记者:写作都有一个符号,比如说你的家乡庙坎就是一个符号,这个符号传递出的信息是什么?
尹马:庙坎其实就是故乡。因为你没有长期生活在那里,而是在城市里面,虽然一个多小时能够到达,但是它确确实实是一个“故乡”。首先,它是你的出生地,其次,它是你长大的地方。因为“回不去”,它在你心里已经不同程度开始陌生化了,但是那个地方它还住着我的亲人,住着我的发小,住着和我一样一年回去几次的这帮人。
我们在乡下长大,其实我们能积累的东西,除了小时候学到的生产技艺,就是那些谚语、童谣,它们构成庞大的乡村记忆。这是我写乡村的语言谱系,它包括语言结构、语言色彩,这种谱系称为乡土经验。
记者:这种语言谱系我们理解为“乡音”,它能够帮助与乡村密切联系的人梳理自己的境遇,当把这些境遇作为写作题材转化为作品,作品的主题就能与读者垂直相见。
尹马:比如,《从我手中接烟的人》这篇散文,主题是重返故乡。我每次回去,都会给村子里的人发烟。他们从我的手中接过烟的时候,说过一些什么样的话?抽烟的神态是什么?抽完烟怎么样?从我手中接过烟的这些人他们又有什么样的故事?叙述方式的起承转合已经不仅仅依靠语感来完成,而且也需要心感。
在村子里游来游去就游完一天的老人,我发烟给他们抽,听他们摆龙门阵,发现他们其实很孤独、很落寞。从外面打工回来的这一帮人,我跟他们在一起抽烟,听他们讲从一个工厂跑到另外一个工厂的故事。年轻的一代有的出去打工,有的出去读大学,他们同样也会抽烟,但他们从来不会主动跟你说一句话,你问他们的梦想是什么?他们说我没有梦想。这一群人就是我们的子女,这是真真实实的事情。
记者:这些描写特别有意思,你想通过作品告诉人们,故乡就是这个样子?
尹马:我洞悉他们的生活,把他们的生活状态写出来,提供一扇观察故乡的窗户,透过这个窗户看到的故乡,其实不应该是这个样子。为什么我要写《回乡时代》,其实我是在召唤人们回来,要他们带着项目回来。当然,我认为乡村要振兴,不只是产业的振兴,更是人才的振兴。《回乡时代》的核心就是重返故乡,即重新回到故乡去。
乡村在变化
但文化是一种定力
记者:当你讲述这些乡村生活时,我们的孤独感一直在弥漫,我们也一直在想,这种孤独来自哪里?
尹马:文化的失落与孤独!把文学放在文化范畴来谈论,是合时宜的。在呼唤重建乡村世界的时候,也要呼唤乡土文化的重建,文化是根,是一种存在着的定力。
 尹马的著作《回乡时代》,召唤人们回到乡村,发展乡村。
尹马的著作《回乡时代》,召唤人们回到乡村,发展乡村。
文学能让人发生意识上的转变,是因为文学让人看到真正的深层次的东西。但遗憾的是,今天读书的人太少了。虽然《回乡时代》的销售量还不错,但真正读完的人仍然是那些从事文学生产的人。普通人也有买的,但读完的肯定很少。文学这道认知世界的窗口,很难被打开。
记者:你所生活的乡下,或者是你称为故乡的地方,文化产生的影响是否是有限的?
尹马:文学艺术的发展肯定是对一个地方的人文精神的重建,但在一个信息被泛滥推送的互联网时代,很多人得不到应该得到的精神养分。当然,作家为了获得流量,也可以把自己的作品写得喜闻乐见。但是,然后呢?
作家写的作品,生活在乡村的人不一定全部读得懂,这种现象是解决不了的。我最近写的十几篇长散文,有很多都是民间故事,写得很通俗易懂,媒体传播阅读量也不低。
我为什么要回到故乡,我为什么写我的故乡?我所写的故乡不只是我的故乡,还是中国广大的农村。
记者:文学的另外一个功能可以说是滋养吧,但在当下,越来越多的人在短视频的快餐文化中失去思考,乡村文化的重建面临很多的问题,我们的方法、路径在哪里?
尹马:我们还是要在全民阅读上下功夫,不管运作下来有没有作用,但氛围要先营造起来。为什么这些年有乡村书屋、农家文化广场,我曾经提过用上夜校的方式来普及老百姓的文化,让老百姓从《三国演义》学生版读起,让全民阅读成为常态。我曾经提出过一个思路:乡村由专人负责,把读书书目发到群里,不定时提问阅读文章的感受,通过回答问题来换积分,推动全民阅读走深走实。
这些年,镇雄的文学艺术创作对乡村重建还是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比如镇雄县摄影家协会一直在把我们的美景、人文展现出来,让外出的人知道我们镇雄有多美丽,知道镇雄老百姓的生活发生了可喜的变化。
记者:当“三农”工作重心从脱贫攻坚转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文化振兴作为乡村“五大振兴”之一,文化为乡村振兴提供了一种定力,未来的创作,你有何打算?
尹马: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扎实推动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可见,文化在乡村重建中的价值和意义。所谓文化,我理解为一个社会过日子的方式。比如在乡村,乡村文化是世世代代的农民与土地打交道,由此产生的风土民情、风俗习惯、民间传说等。这些文化,一方面存在于农民的记忆中,另一方面又成为农民的精神追求。
但现实是年轻一代外出打工,使他们失去与自然和农业接触的机会,乡村文化正一步步远离他们的生活,对乡村的认同感也正一步步淡化,越来越多的社会问题难以找到解决的途径,因此,转而向文化寻求解答成为一种必然选择。
说实话,我好久没有写东西了,我在谋划一篇关于民族民间文化的系列散文,如果能够写出来,我想,一定程度上能增强人们对乡村文化的认同和自信。文化重建是乡村重建的重要部分,回乡的召唤也应该是文化的召唤。

昭通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汪舒 田朝艳 曹阜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