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09-12 08:48 来源:昭通日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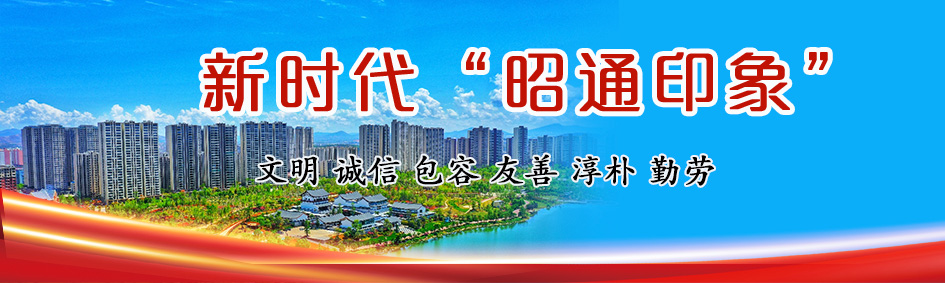

在我儿时的记忆里,父母对我们六兄妹的教育方式是截然不同的。父亲始终恪守“黄荆棍儿下出好人”的教育观念,小时候因做错事挨了父亲多少顿打已记不清了。然而,我们对父亲除了充满敬畏,也逐渐明白了什么事该做,哪些事千万不能做。
母亲则不一样,她总是唠叨着“勤谨、勤谨,衣食齐整,疏于懒惰,挨饥受饿”“养儿不读书,不如喂头猪”“刀儿不磨会生锈,人不读书会落后”……这些我们听起来似懂非懂的话。
我在永善县米贴村小学上三年级的时候,一天下午上写字课,墨盒(一个将墨锭在墨盘里磨成墨汁,倒进母亲向别人要来并铺上棉花的“百雀羚”盒子)不见了,我一边翻书包,一边心里纳闷——书包是开学前几天母亲从供销社买布缝的,没有破烂的地方……张翼老师突然在讲台上大声问我:“你为什么不跟着写?”这时,有个同学说:“老师,下课的时候我看见有同学把他的墨盒拿走了。”我跑过去,一眼就看见墨盒盖子上我用刀尖划上的“王”字,便不由分说地欲拿走,但那个同学用双手死死地按住墨盒,我顺势给了他脸上一拳头。张老师拉开在地上扭打成团的我俩,我才发现他不停地用衣袖揩鼻血,张老师“命令”我赶快拿着教室墙角的搪瓷盆去水池里端盆水来给他洗鼻子,并让我站在讲台右边,面向全班同学站15分钟!
我决定不去读书了,但又怕父亲的“黄荆棍儿”,便仍然早早地起床背上书包“上学”去,等到同路的伙伴们回家后,我才屁颠屁颠地跟在后面回家吃午饭,下午上学依然如故。那天,我背着书包刚跨进门就看见张老师正在和父亲说话。张老师起身拉着我的手并拍了拍我的肩膀说:“你是班干部,怎么可以出手打人呢?他悄悄拿你的墨盒用是不对的,我已经当着全班同学批评了他。人人都会犯错误,改正就好,明天按时来学校上课,我在学校大门口等你。”
张老师走后,父亲那顿“竹尖炒火腿”让我“吃得安逸”,正在灶房里做晚饭的母亲听到我的叫声,立即跑来挡住了父亲手中高举着的竹棍,一边用衣袖为我揩眼泪一边说:“养儿不读书,不如喂头猪。张老师这么远来告诉我们你逃学,你爹不打你才怪。从上一年级我就随时告诉你要好好读书、多识字,别像我们一辈子都是‘睁眼瞎’。”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不是因为背上、腿上痛睡不着,而是心里总在想,我在父母的心里还不如一头猪吗?妈妈的眼睛分明是好的,我们一家人的衣服缝补都是她夜晚在煤油灯下完成的,若是睁眼瞎,还能做针线活儿?
好景不长,我还在上四年级时,学校的所有班级一下子全都停课了,我们只能茫然地背着书包回家。那时生产队有规定,孩子必须年满12岁才能参加集体劳动。母亲又唠叨了:“勤谨、勤谨,衣食齐整,疏于懒惰,挨饥受饿。不读书了,每天放牛割一背草或捞一背树叶倒进牛圈里的活儿算你的,多积点肥交给队上,到时候多有点工分也好。”
时光犹如白驹过隙,我陪黑牯牛的3年时间一晃而过。1969年,学校复课后,我一步跨进了初中。开学第一天,母亲将我拉到她面前,将新书包挎在我肩上,摸着我的头说 :“儿啊,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你一定要好好读书,记住了吗?”我点了点头。然而老师教的初中课程内容于我而言,无异于“坐飞机”,好在有班主任赵和初老师竭力帮助,为我开“小灶”——每天完成小学、初中两份作业。1972年,我顺利考进永善县一中继续上高中。
随着年岁增长,我了解到母亲1930年出生在一个叫硝水堰的普通农民家庭。20世纪40年代的中国农村,像母亲这样的家庭是不可能送她上学的,后来她认识的一些字也是从后期开办的农村夜校里学到的,但她常教育我的那些极富哲理的唠叨是从哪里学来的,成了我心中的不解之谜。
1978年,我到县城工作,离家时,母亲又唠叨了:“儿啊,你已长大离开家了,虽说好男儿志在四方,但是你必须记住,吃水不忘挖井人,一定要认认真真工作,有空还要多读点书,活到老学到老,刀儿不磨会生锈,人不读书会落后……”在妈妈的唠叨中我埋头往前走,转过山梁时回头看,她还在掠起围腰揩眼泪,我将母亲的唠叨牢牢地记在了心里。之后的30多年里,每逢回家探亲,临别时母亲依然这样唠叨着,但我再也不会觉得她啰唆了。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母亲的人生定格在了88岁的年轮上,母亲慈祥的面容深深地刻在了我的脑海里,再想听妈妈的唠叨已成了奢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