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06-27 08:00 来源:昭通日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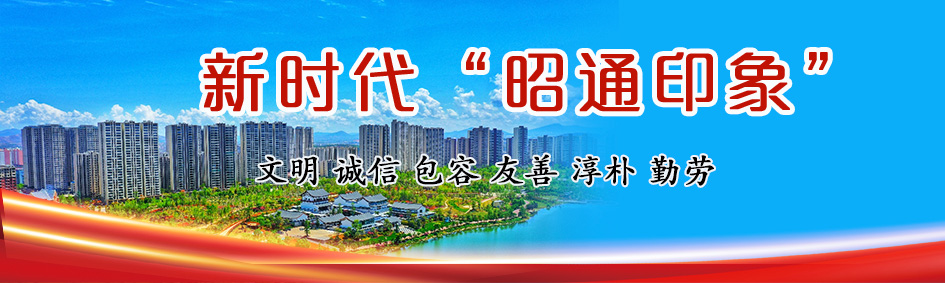

雷平阳让我遇见了诗歌,雷平阳的诗歌让我认识了自己。
作为一名来自昭通的本土诗人,似乎只要雷平阳开始执笔,便被赋予了某种天然使命。然而,当我真正进入雷平阳的诗歌,却惊诧地发现,他的诗歌仿佛有永远的暮色,在无边的苍茫中窥见人生的踪迹以及神的训谕。
雷平阳对母语、文化、地方性有着“山野土著式”的虔敬。面对着那些沉暗的异乡人、出走的人、再也回不到故乡和旧地的人,雷平阳只能用“经书”一样的祷告发声。他诗歌里的冷静、朴拙和沉暗的本质色彩让高山的亲人们,在黄昏下熠熠生辉。读雷平阳的诗歌,我前所未有地感受到从小生养我的乌蒙大地,自黄土地里迸发出的强大力量。它在那儿,召唤着离家的孩子早日还乡。
诗人雷平阳承担的,是把那阵回响带到我的耳旁。
我一抬头,坝子上的亲人们在等待着。
雷平阳在《亲人》中似乎无节制地宣泄着这份情,他的爱表现得狭隘又偏执。“我只爱我寄宿的云南,因为其他省我都不爱。我只爱云南的昭通市,因为其他市我都不爱”,唯有这样的偏爱,才能让昭通母亲感受到。
我不禁回想在生养我的十八年的岁月里,她都太肃穆了,这个老母亲只是靠无言的劳作供养着我。看着我慢慢长大,然后目送我离开,始终不说一句话。十八年来,我饶恕了自己竟然从未好好看过她,没有好好爱抚过她。我习以为常地接受了她孕育的白鹤滩和向家坝,遗忘了老祖宗留给她的盐津的五尺道和豆沙关,忽略了革命先烈们在镇雄、威信、彝良留下的历史痕迹。我暗自担心,我忽视了兄弟姐妹们的那些年,她会不会怪罪我。如今,我只想先走遍云南的每个角落,寻找我的云南记忆,只有借助它们,我才能找到真正的自己。然后,把根牢牢地扎在云南的土地上,我才能拥有足够的勇气向上生长、向外探索。
雷平阳“亲人系列”的诗歌自然避不开字字血泪的《祭父帖》,雷天良死后才算清了那笔糊涂账,最后才从雷天阳变回了雷天良。诗人让他在诗歌中重生,回溯了雷天良因为疯狂地向往着生,所以肉体和精神上双重卑贱的人生。他似乎从一生下来就含着悲苦,“第一声啼哭便满嘴尘埃”“像老农夫的父亲,心有不甘,隔了一代,又跑回来索取被扣下的盘缠”,雷天良的一生从此被打上烙印。老实卑微的农民一生不识字,字斟句酌地讲述苦难。把干净的骨头放入脏水,洗了一遍。像一只田鼠,听见地面走动的风暴,主动跑了出来。后来经历饥荒,弟弟递到嘴边的肉,让他哭得毫无尊严。一个还没有嚼完黄连的人,一个想逃往天堂的人再一次被为生而生的生扯了回来,从此活在了墓地上。再后来,“我”回到家,叫他爹,他不理。走近他,发现他在洗伤口,“一盆的红,血红的红”,雷天良患上了阿尔茨海默病,连“灵魂也走丢了”“他的一生就是,自己和自己开战”,可事到如今,还要打什么呢?还能打什么呢?最后由弟弟给他关上了浮世的门。雷天良的一生,历经贫寒、饥荒,到头来,只有当灵魂出走,“浮世才如他所愿,等于零或比零还小一点”,他终于静静皈依他耕种了一生的那方土地。《祭父帖》饱满深情地记述了父辈的苦难,荒诞而坚强,却也充斥着诗人作为一名儿子的追忆和遗憾。那个叫雷天良的人,尽管从未与之谋面,我却仿佛能透过文字看到这位父亲的轮廓,一个挥舞着锄头的农民,一个为了生而拼命挣扎的男人,最后尘归尘,土归土。平凡又渺小的他,浓缩了一代土生土长的昭通人的影子,他们似乎活得卑微如尘埃,一辈子跟高原上的土地贴在一起。可是,正是这样的山川之下,孕育出了顽强坚韧的生命,他们毕生的追求是——活下去,好好活。他们只是恭敬地接受每日分配下来的累,他们平静地承受着生活带来的苦难和悲哀,然后等着第二天的到来。黄土地上的亲人们啊,为生而生的人,这份对生的敬畏,将穿透黄土地和座座高山,延续到后辈们的生命里。
《背着母亲上高山》中,诗人从母亲的视角,再次回归乡土。“背着母亲上高山,让她看看她困顿了一生的地盘。”浩浩历史长河,昭通人民在你的守望下长大,度过漫长岁月;最后,又站上这座高山,反过来守望着你,献出了自己一生的重量。回归这片乡土,所有的痛苦与不平都将在这里得到抚慰和消弭。雷平阳在诗歌中写道:“我的焦虑则布满了白杨之外的空间,没有边际的小,扩散着,像古老的时光,一次次排练的恩怨,恒久而简单”,那些自以为迈不过去的坎儿,都在她的慈悲下磨平,被她的宽容和纯粹感化,一切终将释怀。我那不善言辞的老母亲,笨拙地开解着我,迎面吹来的风、泥土的芬芳、粗犷的方言,让我在如同浮萍般飘忽不定的尘世,找到了歇脚之处。我的昭通,祖祖辈辈生活的乡土,一代又一代人延续着你传承下来的美德。他们平静地经历和接受,和这片坝子一起从容地承载着所有的苦难与美好。再借一支山歌,在群山间一遍遍回唱。
昭通因沉寂而隐秘,也因沉寂而伟大。那养育了世世代代人的一方水土,在处于相对隔绝却又因此更加肃穆苍茫的高原地带,无言地塑造了厚道的昭通人民。他们敬畏着生命运行的准则,却也从未停止在高山黄土之间释放自己磅礴的生命力。高原气候孕育出的人民,天然有着坚韧刚强的力量,能够经受生命带来的厚重,也因此能够承载由它带来的欢喜。雷平阳在诗歌中所说的“原本山川,极命草木”,便被赋予了另一层含义:昭通人民生于高原,最后又化为草木尘埃反哺这片土地,祖祖辈辈沿袭下来的精神与信念滋养着后代,流经所有昭通人民生命的金沙江始终奔腾不息。
一路风尘仆仆,可兜兜转转,终究还是遇见了雷平阳的诗歌。如同途经金沙江畔,从里到外被洗刷干净,我终于看见自己身为昭通人的质朴属性。我于是在雷平阳的诗歌里找到了归宿,汲取力量;山高路远,土生土长的昭通孩子,无论走了多久,还是要回到云南,回到昭通,回到母亲的怀抱。
此刻,隔着一百多公里的距离,我看见挂在枝头的昭通苹果,它们与故土的亲人们,向我发出了悠长的召唤。
在苹果掉落之前,我要把它们全部接住。

作者:杨 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