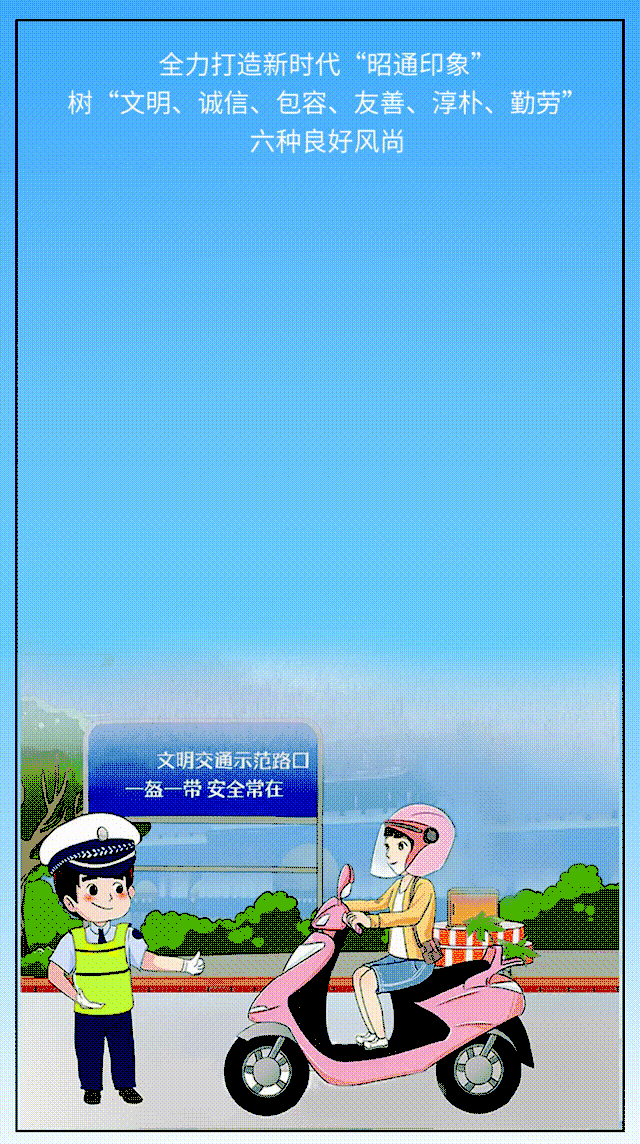2024-05-31 10:06 来源:昭通新闻网



家乡的山,那些刚劲而挺拔的线条,是植根于我灵魂深处的坚韧,它以特有的险峻让我用一种仰望的姿态端详,孩提时那稚嫩的信念和梦想就从这里飞出。那时候,我的眼里只有青天和白云,那些轻轻柔柔、千姿百态的云朵是我最绚丽的梦,它以最轻盈的步伐、最曼妙的舞姿点缀着断崖上倒挂着的那些知名或不知名的树,那是我视野的极限,我只知道,在断崖之上的部分,是天。天外面呢?爷爷眯着眼,抚摸着山羊胡须慈祥地说:“不知道,以后你自己走出去看吧!”在儿时的梦想里,是多么渴望飞出这片天。

乘风破浪,十年,颠沛流离,又是十年。再次回到这里,搬个小板凳坐在矮平房上仰望这些山,青山依旧,断崖依旧,朝晖夕岚依旧,鸟鸣虫唱依旧。从竹林的斜影里看雾岚散开,山的影子从模糊到清晰,从块状到线条,那些植被的层次越来越分明,新的一天又开始了。我尝试着在酒精的刺激下,再去寻找那些儿时的憧憬、那些少年的梦,看着视野的尽头,顿觉恍然,其实,我更喜欢这天边的界限。
在这个翠色欲滴的盛夏,那些沁人心脾的绿野是牛羊的天堂,牧羊人的吆喝声打破了山的寂静。在这个通信技术已经高度普及的时代,突然听见一声呼唤:“哎……回来吃饭喽……”那些积淀于心底最柔软的地方被亲切地唤醒,不觉潸然泪下,原来,在物欲横流的红尘,我又过了十年。

鸟径横绝山巅,我小心翼翼地行走在路上,步履竟然比儿时蹒跚,我成了这座山的客人,似乎是对这些年成长最大的讽刺。凌晨,躺在床上计划着今天的柴米,我已经失去了在这块土地上赖以生存的物资,只有从山外购回。门外,二叔的狗欢叫起来,打开门,我禁不住狂喜,一篮子土鸡蛋、莴苣、土豆,这些都是我满足口腹之欲的必需品,二叔坐在走廊下平静地说:“刚才你四伯来过了,知道你还在睡,就把菜放在门口了,等一下你把菜捡了放着,把篮子送回去,如果想吃四季豆,我地里的熟了,自己去摘。”我有些愕然,突然想起了在菜市场跟我讨价还价的小贩和那些掺假的食品。正想着,二婶端来了一碗热气腾腾的水豆花说:“今天我们推豆花,给你端一碗过来。找个碗腾一下,碗我还要用。”在这里,推豆花、煮凉粉这些工作量比较大的烹饪活动,在农忙的季节是很少做的,所以,谁家做了,就会用碗给每家都送一碗,而这个习俗,离我已经过去了二十年。
母亲的病房总是最热闹的,我一直认为母亲在生命弥留的时刻需要静养,可是无法拒绝乡亲们的热情。打开了话匣子,我才发现我所学的语言竟是那么苍白,他们最温馨的安慰,竟然让母亲在超乎寻常的痛苦中安静了下来,卧床月余的她,突然想起来走走,想呼吸一下室外的空气,想去看看她的长眠之地,静静地听着父亲为她念墓志铭,脸上居然有了笑意,说:“谢谢你们!”这是我从未有过的震撼。

一直偏爱那条河,清澈透明的水质,哗啦哗啦地流淌在我记忆的深处。有人说溪流是智者,它从来不走错一步路,任何人为的改变都会破坏河道原有的美感,欢快的歌唱伴随着粼粼的波光,点缀着碧绿的藤萝,青苔以最优雅的姿态应和着水声,似乎在舞蹈。掬一捧水,想着屈子的沧浪之水,濯缨濯足,释放所有的疲惫和不快,让自己安静地守着、凝视着。瀑布是常见的,有飞流直下的湍急,有飘飘洒洒的细流,最浪漫的莫过于那种悬挂于峭壁的“白练”,有着丝绸般的质地,因为落差太大,从绝壁直下时它不是一种垂直的姿态,而是飘逸地挥洒,似有似无的水雾在阳光下为山谷折射出一片光怪陆离的色彩。安静地坐着,盛夏的酷暑早就湮没在飘洒的水雾里,闭上眼,每一口呼吸都充满清新。偶尔传来一声蛙鸣,也许它们在呼朋引伴,也许它们在传递着爱情。放开怀抱,伸展手臂,没有风,巨大的水流冲击力激荡起的水雾迎面而来,衣袂飘飘,水雾掠过耳际发梢,转瞬变成了一片清凉,每一个毛孔都沁入了一份舒适。偏爱这条河,在这个盛夏的季节。

离开,当山的线条和水的味道在倒车镜里越来越模糊时,我知道,我又一次离开这里了。午夜梦回,依旧清晰,那山,那人,那条河。

郑吉喜 文/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