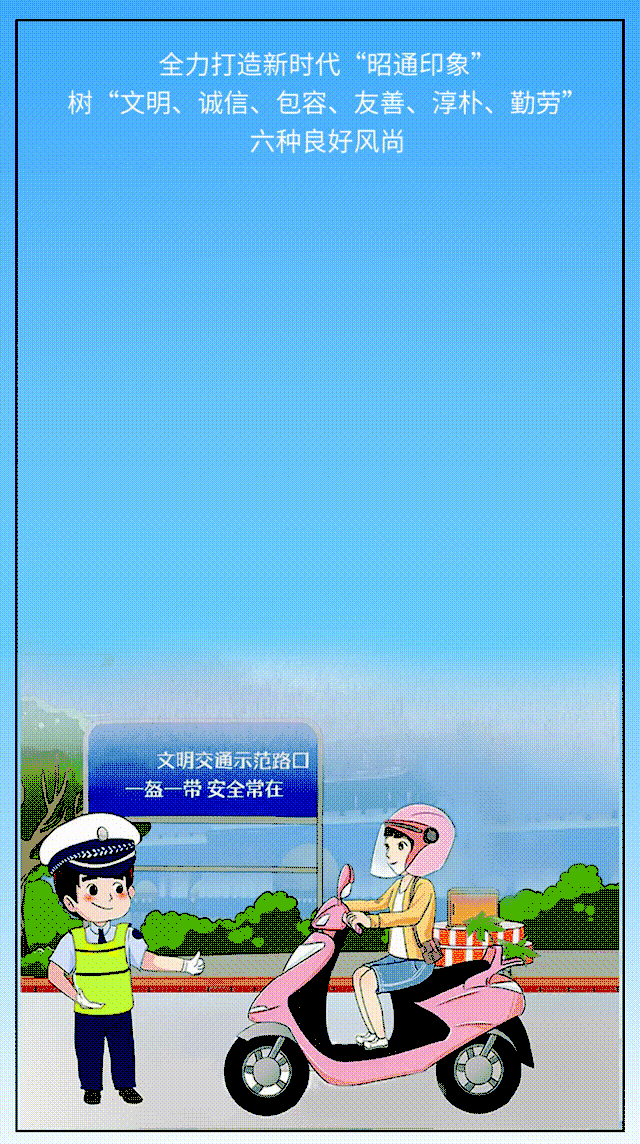2024-05-09 10:00 来源:昭通日报



一
2001年,同时在《诗刊》《大家》《边疆文学》《春城晚报》(整版,配发照片和诗人简介)发表诗歌后,我突然销声匿迹了……2020年,我的诗在《诗刊》“双子星座”栏目发表,同时配发了我的照片和诗人随笔,我在随笔中引用了古语:善不可失,恶不可长。
二
“我遵从重力法则,即地心引力的法则,用我所有的身体所有的力量和我所有的爱”(耶胡达·阿米亥)。理论的缺失让我感觉到写作和思考都没有明确的支撑。自己很多时候都靠感觉或者灵感,而没有更多地思考,甚至不是认真地思考。即使有时候认真地思考,也没有深度地思考,用力地思考。有人挖地300米,你只能挖地3厘米,情况是大不一样的。布尔说:“我在说话时对自己的了解远不如我沉默时对自己了解。”
三
我以为文字始终达不到生活本来的程度。也就是说,文字的喜悦或者疼痛的程度都远不如内心的喜悦和心口的疼痛。文学作品始终达不到人类的要求或需求。而文学的意义就是在适当的时候和人的心灵适当地契合。
四
我只想活着,然后写诗,真的,我这一生已经错得太多,而我的生命其实已经所剩无几。因为我的性格还算开朗,所以除了我的心脏病以外,很多事情别人都不知道,尤其是我内心深处的崩溃。是的,我过得并不如意,经常在睡前迷茫和内疚,每次醒来,胸口都处于疼痛和忧伤的状态,必须找一个理由安慰自己才能起来。谢天谢地,内心深处的善竟然还在,内心深处的灵魂居然还在,所以诗歌又回来了,诗人又复活了。真可谓“善不可失,恶不可长”。我越来越喜欢安德鲁·马修斯说过的一句话:“一只脚踩扁了紫罗兰,它却把香味留在那脚跟上。”现在,我的心终于安定下来。终于,不想再斤斤计较,也不想与人为敌。放弃了消极不良的生活方式,放弃了报复思想。只想与人为善,好好写诗,好好度过不多的余生。如果有一天我悄然离世,不是因为恨,而是因为爱,亏欠之爱!我没有任何理由求得宽恕。“你不快乐的每一天都不是你自己的,你只是虚度了它”(费尔南多·佩索阿)。
五
人活着,总有这样那样的苦,也有这样那样的乐。我们不能因为一条路上有一个坑塘,就否定了这条路;一张白纸上有一个黑点,就认为整张白纸都是黑的。写诗的时候你是一个诗人,可是写完以后,你可能是另外一个人。你有满意的自由,别人也有不满意的自由。“一个人感觉合脚的鞋却会夹痛另一个人的脚”(卡尔·荣格)。
六
唉,不知为什么,此时此刻莫名其妙地想起自己以前写的诗《狗眼看世界》:我梦见全世界都是咬人的狗/醒来时发现自己也是一条狗/用牙齿紧紧咬着自己的舌头。
七
2020年,新型疫情令人忧心忡忡。向包括中国在内的全世界因疫情逝去的生命表示沉痛的哀悼!2020年,再蓝的天空好像没有诗意。2020年,总感觉有石头压在心口上,呼吸困难,胸前区继续疼痛。这场灾难中最好的人是谁,大家有目共睹、心知肚明、刻骨铭心、感恩涕零!什么样的国家,什么样的制度,什么样的人权,大灾大难面前一目了然。生命不分黑白,不分大小。听闻全球各地生命的不幸消息,其实我也疑惑,我也恐惧,我也焦虑,我也怕死,我也纸上谈兵,手无缚鸡之力。纵有一江泪水,也不过是逝者“路上”的凄凄阴雨。
八
你的诗歌可以让你的父母、儿女、学生、老师看不懂,但千万不要让他们感到羞耻!我认为人类第一次用树叶遮住身体的时候,美学就诞生了。
九
我们终将逝去,只要不违法,不伤害别人,即可率性而为,没有必要故意去装这装那。任何人的性格都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低调或高调,内敛或外露,独处或合群,都不代表人品与作品的优劣。唯有实事求是,方得始终。不要轻易相信某些人所谓的淡泊。有的人表面不在乎,却始终窥视着有利于自己的任何机会。
十
诗歌的理论可能已经上千百万,而每一个诗人的感受却不尽相同。这正是希望所在。你已经感到你已经无法克制,你已经迫不及待,所以诗就出来了。技巧就像刀一样,既可以切菜也可以行凶。每一首诗里都藏着一颗心,所以诗心重于技巧。就像每一栋房子里都藏着一个人,人永远重于房子。诗人和木工并没有什么区别。如果有的话,那就是诗人以为自己是神,而木工认为自己是人。在读者面前只有两类诗:懂和不懂;喜欢和不喜欢。而同一位诗人,也可能会写出不同类别的诗。
十一
感觉需要储备,良心也需要储备,智慧也需要储备。一个人,不可能突然就智慧起来,也不可能突然就善良起来,更不可能突然就敏感起来。所以我们的诗歌应该是冒出来的,也就是说像山里的泉水,储备够以后,受到外力的挤压或者自身的充盈,自然而然就流出来了。也就像水龙头,水管里面没有水,你把水龙头打开有什么意义呢?就像水库里面没有水,把水闸打开又有什么意义呢?表面上你只是在写一首诗,而实际上是你的所有积蓄都在发力。
十二
突然想起病逝多年的父亲。我的农民父亲子世沛不懂诗,但懂生活哲理,他说:“人吃三碗饭,不能全都变成屎,要让一碗变成智慧。”他还说:“洗脸要洗耳朵,扫地要扫旮旯。”
十三
我多么希望我的每一首诗都是我的临终遗言。海子曾说:“从荷尔德林我懂得,诗歌是一场烈火,而不是修辞练习。”卡夫卡把语言视作生命,把每一次动用语言看作一种新发现,但始终认为写作本身就是一种耻辱,而“诗歌就是疾病”。
十四
“在世界面前,莫让我感到愧疚,我的损失,我的苦恼,于它是尘粒之尘粒”(泰戈尔)。可我的一世已经是愧疚的一世,是我辜负了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辜负了绝无仅有的时光与生命。即使我的内心每天都处在疼痛与焦虑中,即使我死于非命,仍然不足以惩戒我的草率与极端。在亲人面前的我已经不是我,在外人面前的我已经不是我,在我面前的我也不止一个我,那么在祖国面前的我还是我吗?
十五
最好的诗莫过于“还活着”。一个人成为诗人,很可能是诗歌的幸运,甚至是一条街的幸运,但也可能是另一个人甚至一个家庭的不幸。
十六
其实一个人真正的故乡,就是自己的母亲。也许有人会反对这种说法,但我认为:所有的观点,都是偏见,没有偏见,哪来的观点。
十七
突然想起2001年在一次文学笔会上的发言稿《让个性穿越理想与善良》,其中写道:文学的兴衰,标志着一个时代的品质。诗歌必将成为人类告别世界的最后祭礼。至于个性或风格,其实是一种“我”或“排它”,这完全是内在的需要。结构必然有它满足意义的文本,而事实是远远满足不了意义的原生性与不确定性。这也正是创作在形式和文本上的尴尬,也是写什么与怎么写之间终极对接的可能与障碍。人的社会性是不可动摇的,而个性化的突出特征从来都是源于社会的变革,即一个时代与另一个时代的作家的区别是一目了然的。我们不能欺骗普遍的意识,又必须站立在普遍的意识之上。任何作品都存在读者挖空心思要得到或证明的成分,也完全存在几年,甚至几代人都不可能探测到的某种。因此,读者完全有必要自作聪明。但必须清醒的是,门的意义并不在于让更多的人进去或者出来。无论在公开的经纬度,还是在光亮的隐秘地带,作品都绝对不是强烈震撼广告中的假酒。容不下问号的年代,我们惊恐万状。容不下理想的年代,我们更是悲痛欲绝。当我处于几乎爆裂的急迫感或者静若止水的休眠期时,游离的精神与肉体便开启了崇高或卑鄙的大门,于是开始写作。岁月的伤痕或者困惑,时代的疾病或者英明,都是活着的双眼跳动的暗环。每一个时代的每一个人,都曾经生存于逃亡与凝滞的混沌之中。写作,就写作者而言,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有序的回避。而作品则与此相反。任何作品都是切入的,上方或者下部,皮层或者内核。这正好粉碎了作家自身可能的躲避计划。写作,就在这样一种矛盾或窘境中对抗着、宽恕着、吐纳着。
十八
突然想起,1998年给一家杂志写过一篇创作谈,其中写道:我们及我们的文学不能也不可能消除、排斥圆润的、细长的、霸道的、致命的。这就迫使我们必须经历一棵树在沙漠中的劫难,才能感悟到日常生活中水的最高品质。
我们需要进补的不仅仅是肉体。近距离的贫血观念忽略了另一种更为虚脱的弱面。肉体欲望的高度膨胀,使得心灵不堪一击,甚至不复存在。虽然,自有人类以来的任何时候,都幸存着某种高于物质的信仰,但在某些行为与理念都已变成商业运作的年代,这种信仰尤其显得高贵。关于墨水、关于笔尖、关于电脑、关于纸的类别,包括我,都不是要素。最重要的是,作为汉语作家,我们对汉语的熟悉程度与忠贞程度是否超越了我们对爱情、对金钱的背叛程度。我们面临的困境正如饥饿与粮食。其中的技巧当然是重要的,所谓无技巧,实际上是消除技巧在创作过程中的盲目性与对抗性。
十九
一些作家的修养,在酒桌上原形毕露。在某个圈子里,你是王,在其他圈子里,你就是小丑。作家的作品掩盖了作家自身的巨大缺陷和分裂性人格。
二十
“发现”,对于个体还是整体都是永无止境的。
二十一
我有两行诗,曾经发表在《边疆文学》上,听说一直在流传:你有多少土地/我就有多少种子。
二十二
告诉你一个创作秘密:当灵感来的时候,像洪水,像水库放闸一样涌出来,这个时候你的网截住了其中的所有东西,最后把鱼挑出来,其他都放弃。
二十三
不知道为什么,我特别喜欢艾米莉·狄金森曾经说的一句话:我的战争都埋在诗里。
二十四
生活不是我们能完全左右的,很多事很多物,我们都处于无奈之中,悲的太悲,乐的太乐,穷的太穷,富的太富。软的太软,痛的太痛,贪的太贪,狠的太狠,善良的又太善良。唯有通过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才可能有活路。在不幸与真相面前,当所有努力都宣告失败,只能用命,用命。

作者:子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