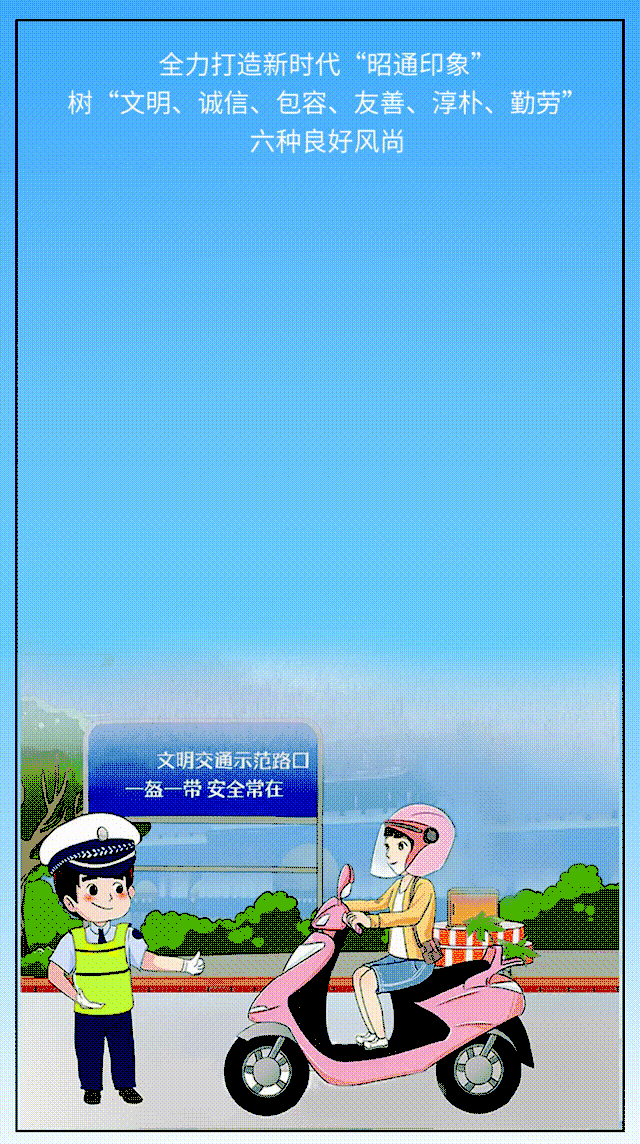2024-04-11 09:34 来源:昭通新闻网



我的故乡在云朵镇。现在的小年轻人,或许只知道“网吧”而不知何为“话吧”。小时候,云朵镇上有专门提供座机以方便别人电话联系的场所,按分钟计费,这样的场所当时被称为“话吧”。
在镇上开第一个“话吧”的是我家,从1998年到2008年,连续开了20年。“话吧”开在镇上两条主街道之一的彩云街上,也没取个什么美称,只是在灯箱上写着“话吧”两个字,挂在门头上,白天晚上都很显眼。蓝色的玻璃门上贴着“诚信经营”4个字。这一开,由第一家首开,到最后一家关闭,一度成了镇上的一个坐标。
那时候,手机的使用不普遍,有很多地方,特别是山镇村乡,甚至座机都还未普及,大家都是使用公用电话,或是到私人合法经营的“话吧”打电话。
那些年,镇上和邻近的乡里连续发现并发掘出不少的煤矿,当时的管理不是很规范、很严格,可以私人买卖、开采。于是,很多乡邻通过经营煤矿或者挖煤卖,赚到了不少钱。镇上繁荣起来了,本镇外出的人、过往的拉煤客、外乡来做挖煤工的、娶去嫁来的媳妇儿们等,都成了“话吧”的常客。
当时,家里一共装了8部座机,每部话机之间,都像现在的写字隔间一样,用木板分隔开。每部话机上都放着一沓拆小的纸和一支笔。那几年,每逢街天,家里总是有很多人排队等待,家里都挤满了人。
那时候,爷爷已是86岁高龄,虽然耳不甚聪目不甚明,但是依旧热情好客,还招呼着给别人倒水、给别人安排凳子。
最辛苦的是母亲。每天早上,她都要把地扫得干干净净的,用抹布把每部座机、每张桌子、每个隔柜区域,都擦得一尘不染,一天也不曾落下,让一切看上去整洁干净。
“话吧”红火时,话费的收入加上卖点零食百货,一个月有三四千元的纯收入,在当时可不算低收入了,供我们一家人的生活开支是绰绰有余的。
那时候,我在县城读高中,每个周末回家一次。完成学业任务后,我常会帮妈妈做些与“话吧”相关的事,因此,也就经常有机会听到一些客户打电话时的辛酸悲喜。
比如,有人发了工资会高兴地跟家人说,然后计划着买电视、给娃买衣服、买几头猪……憧憬着美好的未来,幸福之情溢于言表,让人听了也为之高兴。
比如,一个60多岁的奶奶,老伴有家暴倾向,女儿远嫁江苏,奶奶每次受了气,就打电话给女儿。她拨通了就挂掉,然后,女儿就会打过来,这样就可以省些电话费。电话两端,每次都是一番诉苦和安慰。讲完电话,她还要坐一小会儿,跟我母亲再诉说一番,才颤颤巍巍地离去。想必,每次倾诉后,心里的苦楚也就发泄了一大半,这终成了她的精神支柱。
比如,有年轻的夫妻吵架了,妻子就来打电话给闺蜜,诉说丈夫的不是和自己的委屈。絮絮叨叨说完,突然觉得丈夫也没有那么不好,于是心情轻松地回家了。
比如,在昆明打工的小姑娘,过年回家,穿得花枝招展、化着浓妆来打电话,学着昆明人说话……俨然已是那个大城市的姑娘,如今衣锦还乡,总得跟这里的人有点不一样。
如此种种,不说能看尽世间百态,但至少能说听闻了不少的世情冷暖、人间烟火。
那时候,“话吧”收取的话费是2角钱一分钟。很多年轻人,通常是三言两语讲完了,需付2角钱,没有零钱,就递过来5角钱甚至1元钱,说不用找零,害得母亲急红了脸,坚持要找补给他们。但上些年纪的老人,恰好相反,哪怕是1角钱,一般也要等着找补。有些客户,打了几角钱的电话,会说“改天来给”,母亲也不纠结,因为绝大部分人都会在下次来时把钱付清。
也有比较贫困的老人,颤巍巍地走很远的山路,只为来给儿女打个电话,报报平安。这种情况,母亲一般不收他们的钱,还会倒水给他们喝。到赶街天,家里的四五个保温瓶,都要提前装满热水,玻璃杯都被洗得干干净净,茶叶也会被放在客厅和厨房里的桌子上,供到这里歇脚的人倒水泡茶喝。有些老人没读过书,不会拨电话号码,每次都是拿着请别人写的一张小纸条,上面是电话号码,请母亲帮忙拨号;还有一些人,打电话的时候需要记号码,也请母亲帮忙写。母亲总是耐心地帮他们,从来没有怨言怨色。
当年有人曾给我们家提议说,2角钱打一分钟这个利润太微薄了,不如改成和别家的一样,5角钱打一分钟,反正要打的人还是得来打,并且还方便找零钱,不用到处去换零钱来找给别人。但母亲说他们挣钱也不容易,特别是农村人,一两角钱也是辛劳所得。
在母亲的操持下,“话吧”的人气外溢了,溢成了一种信任和热乎乎的情感,不知从何时起,好多人来“话吧”打电话,就会隔三岔五地从家里背些瓜果蔬菜来,表示感谢。我记得那些年,家里几乎不用买瓜果蔬菜,总是从上一个赶街天吃到下一个赶街天。
后来,我们姊妹几个都在外地上学,家里只有母亲一个人。是这个小话吧带来的人气和左邻右舍的友好,让母亲每天忙碌而充实,没有感到孤独。
母亲常常用这几部座机给我们打电话,她每天都要看天气预报,特别是看我们在的城市的天气预报,如果有天气突变,如降雨、下雪等,她就会打电话跟我们说。
母亲给我讲过一个初一年级的学生,因为第一次离家住校,每天早上6点钟跑早操经过的时候,都要来敲门打电话给他妈妈哭诉一番。每次听到他敲门,母亲总是快速披衣起来,开门让他打电话。他每次都是讲几分钟,花几角钱,等他讲完之后母亲又去睡会儿。她说看着那学生可怜,怎么能不给他开门呢?如果他早上不打电话,估计一天都会难过的。母亲慢慢开导那个学生,让他多跟同学交往,少往家里打电话。后来那个学生电话打得少了,适应了学校生活后还特意来感谢母亲。
2003年以后,镇上的煤矿被开采得差不多了,并且管理也规范且严格了起来,加之矿场里很多都实现了机械化操作,不需要那么多的人工劳力,镇上的南来北往的人少了很多,打电话的人自然也就少了很多。父亲的煤矿因一些原因赔了很多钱,一家人的生活开支全靠“话吧”,“话吧”每月的收入降到1000多块,电话机从最先的8部减到6部,再后来减到4部,到“话吧”来打电话的人越来越少了。
不过,家里人气还是很旺,十里八乡来赶集的人,还是爱到“话吧”喝茶,歇歇脚、聊聊天;不会用手机或者没有手机的老人,还是会来这里打电话。
父母慢慢变老,随着手机和座机的普及以及很多年轻人外出打工,来用公共电话的人,大部分是老人和学生了,“话吧”每个月的收入更少了。
2008年,我把父母接到城里,故乡的房子出租后,支撑了我家10多年的经济开支,供我们姊妹上学,见证小镇上的悲欢离合,见证小镇变迁的“话吧”,正式退出了舞台。
“话吧”给我积攒了不少东西。比如,母亲常说的“多栽花,少栽刺”,父亲常说的“如果老一辈爱帮助别人的家庭,后代生活都要好一些”等话语,一直影响着我。
偶尔回到故乡,看到那个写着“话吧”的灯箱还挂着,似乎又看到那些人们谈天说地的场景,看到那些悲悲喜喜的面孔,看到那些20多年前的时光。

作者:解彩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