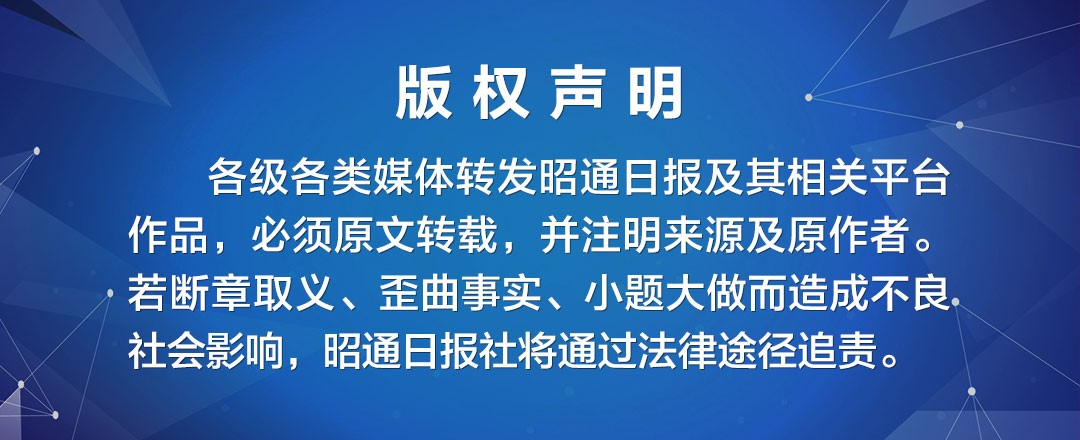2021-08-02 11:35 来源:昭通新闻网

你可曾见过一只骄傲的恐龙,它身长27尺,从侏罗纪时代走来,自由地穿行在威信水草丰美、万壑争流、阳光四溢的原始沃土上。它若奔跑,群山会发抖;它若长啸,众鸟会惊飞。
也许,它和族群走散了;也许,它想另拓疆土;也许,它奔着这片原始沃土上的“席位”而来。当人们找到它时,它已在威信县扎西镇大河村邱家沟的山坡上足足沉睡了1.8亿年,庞大的身躯依旧保持着骄傲的姿态。北京博物馆,成为它第二个长眠的故乡。
在镇雄,人们发现了犀牛牙化石,形成于5万年前。在威信,人们发现了新石器时代的骨针、熊猫、马鹿化石,形成于5000多年前。在这两个县,分别出土了一批批来自西汉、明、清时代的古文物。
有一条河叫赤水河。骄傲的恐龙曾弯下身躯,大口大口地吞咽它的甘甜,狂躁的犀牛曾在它奔腾的河水里撒泼打滚。就是这样一条河,在公元前135年,酿造出了令汉武帝赞叹为“甘之美”的赤水枸酱酒。
从赤水源头镇雄出发,赤水河流经威信,孕育了当地厚重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润泽了一方沃土。苍翠的群山,自有花鸟虫鱼相伴,彝族人民在此土生土长,汉族、苗族、白族人民为它迁徙而来。他们沿河繁衍生息,与天地万物相遇、相知、相爱,活出了每个时代独有的性情和模样。
城堡,城堡
天绞云,雨淋淋。
雨水沿着十来米宽的屋檐流淌,瓦片纹丝不动,任随它在陶帮华家老宅上空飘落,洒向山下连绵不断的赤水河河面,淋湿了一个又一个觉醒的时代。
屋檐下方由一块块大石板铺成的院坝上,有一排比女人的酒窝还要深、还要大、还要圆的小石窝整齐地排列着,滴答滴答……在这里,水滴与石板较量了300多年,陶帮华家14代人可以做证。
陶帮华家所在之地,是一个苗族聚居地,地处云南省昭通市威信县双河苗族彝族乡半河村,以陶姓为主,寨名叫厚房。

厚房老屋基四合院和城堡城门。
陶氏家族原籍湖北麻城,明、清时期分别经四川、贵州迁到威信水田湾子。300多年前,陶氏家族中一个叫陶一锁的人,与镇雄坡头陇氏官家小姐私定终身,搬迁定居至厚房,从此便拉开了厚房历史的序幕。
厚房的故事与战争有关,与一座军事城堡有关,城堡就在陶帮华家隔壁。
精雕细琢的吊脚楼,厚实坚固的石头城墙,看得见的碉楼与炮房,看不见的隐秘军工厂,曾是这座城堡独有的符号和秘密,是一个独一无二的存在。
城堡的主人叫陶正清,生于1878年,是厚房陶氏家族第五代传人,是继父亲陶洪富之后第三任清王朝团首。因与兄弟陶正超聚敛了大量财富,为保财产安全和巩固其统治,耗资白银上万两,于民国十二年(1923年)从四川请来了一批工匠,在厚房老屋基修建了这座城堡。
城堡占地3600平方米,由一栋四合院吊脚楼、城墙、四座碉楼组成。吊脚楼为木质结构,门窗上的图案精雕细琢。外围是1.4米厚的石头围墙,高大坚固。城墙的四个角均有碉楼,主碉楼高7层,左角碉楼高3层,后面两角碉楼高2层,4座碉楼均有交叉火力枪炮眼。加上厚房天然的石林战壕交错,且有地下溶洞可伏千军,厚房的防御简直是固若金汤、坚不可摧。
如果说战斗曾让这座城堡保持了最旺盛的生命力,给它堆砌了一副铁石心肠的模样,那么吊脚楼里的雕刻,则赋予了它最温情的一面。
走进吊脚楼,历史的笔触隽永而深邃地雕刻于此。房子正厅三开六扇的大门上,雕刻着刘备、关羽、张飞、马超、黄忠等三国人物;正厅天花板上雕刻着二十八宿、十二宫辰、八仙过海、二龙戏珠、双凤朝阳套八卦图等图案;正厅外柱上雕刻着左虎右凤图案;下厅内门上雕刻着自秦汉以来二十四帝的长匾肖像;左、右厢房大门和花窗上分别雕刻着晋、隋、唐、宋、元、明等历史文臣武将的肖像……站在这一个个惟妙惟肖的人物雕像前,每一幅都那么有趣,没有谁愿意将它们与窗外的喊杀声联想在一起。这一扇扇文化之窗,让我们看到了厚房在民国时期财富与文化的高度交融。
躲过了战火的焚烧,还来不及、也舍不得告别这一身荣华,历史的尘埃已纷纷扬扬地散落到吊脚楼的每一个角落,与蜘蛛网交织在一起,给这座吊脚楼披上了一件落寞的纱衣,唯有门窗上的张飞,手握长刀瞪圆了眼,直视着吊脚楼的过去。
那三开六扇大门里住着的人们,亲手推开了通往历史的大门,追逐着时代迁徙的光影,是对、是错,被指责、被遗忘,被敬佩、被追忆……历史一边给出答案,一边又留给后人太多的谜。
修建城堡的四川工匠,他们用多少时间完成了全部的修建?在厚房的这段时光,是否让他们终生难忘?苗家的酒,他们一定醉过;苗家的糍粑,他们一定吃过。
每一块石头都有它的宿命和使命,哪怕是沉睡了千年万年,也愿意为了一场短暂的相遇迁徙而来。除了城墙,吊脚楼的院坝也是用一块块长方形的巨石铺就的,平整的石面全是手工打磨,细锤细錾的痕迹已被时光磨平,但依旧坚固如初。
这些巨石从哪里来?它们是否经历了艰难的人背马驮?又或者,是它们沉重的迁徙,筑就了一座城堡,成就了一段历史,成全了一个民族。
厚房城堡四合院吊脚楼。
如今,城墙已残缺,大门门槽犹在,落寞而孤独。门槽宽1.3米、高2.74米,门槽上方拱形石头上“团风永振”的大字还在,大门左右的石柱子上刻着“才德兼全可靠下东区长、公平正直方可为二甲绅粮”的对联,这副草书对联是当时的州府赠送的。
对联中提及的“下东”指的是一个特定的区域,包括当今的威信县旧城、双河、高田、罗布等乡(镇)。在清末时期,行政区命名分别为一甲、二甲、三甲、四甲,对联中提及的二甲即今天的威信县双河苗族彝族乡。由此可见,陶氏家族当时的地位和势力还真不小。
1937年,陶正清的独子陶著煊继任双河区区长和民团团首。
触摸着坚固厚实的门槽,遥想着当年这里门庭若市的光景,那些出入大门的身影幻灯片一样影映在脑海中。是啊,他们从大门里走进去、走出来,也曾儿女情长,也曾豪情万丈,各自穿梭在历史的尘埃中,完成各自的使命,又共同走过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这段岁月,不为人知,却又鲜为人知。
厚房特殊的地理位置,促成了殷禄才和陶著煊的相遇。随着扎西会议的召开和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由殷禄才领导的云南游击支队把厚房作为重要通道,厚房的苗族民团也是游击队坚定不移地做好民族团结工作的重要对象。
一天,殷禄才一行人带着烟土和礼物,拜访厚房(双河区)区长兼民团首领陶著煊,并参观了民团坚固的驻地、兵工厂、炮房、碉楼,观看了教场上操练军事的团兵们。
兵工厂在厚房的这段历史中,是一个传奇的存在,它的隐秘不言而喻。兵工厂由厚房民团在岩洞里秘密组建。当年,陶著煊安排陶发祥带着殷禄才去参观兵工厂,眼前的一幕让殷禄才激动和感慨不已:足足300平方米宽的岩洞里,摆满了一些基本成型的机关枪、冲锋枪、步枪、短枪和手榴弹,手榴弹上还刻有红色的五角星。陶发祥分别给殷禄才介绍兵工厂里几名外地的造枪技术工人万国成、万国义、向付初、周发财、王支荣及当时本地学徒古成宣、古成和。殷禄才分别与工人们热情握手,并详细了解武器的生产情况。
参观完兵工厂后,陶著煊热情地款待殷禄才一行,并挽留他们在寨子里过夜。陶著煊是个聪明人,他明白殷禄才此行的目的和话里的弦外之音。
那一夜,厚房所有的画面在殷禄才的脑海里回放了一遍,他可以安心地睡上一觉了。对于一个在枪林弹雨中奔跑的勇士来说,这股革命力量激励着他继续向前。触摸着白天他和陶著煊彼此握紧的双手,余温还在他的手心未曾散去,因为在厚房,他们建立起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次日早上,殷禄才离开厚房时,陶著煊赠送他10多支枪和2000多发子弹。
吊脚楼的外墙上,挂着“半河乡革命委员会驻地旧址”的牌子,这里是川南游击纵队的驻地,威信县委、县政府于2011年在此挂牌。
说它传奇,因为这在苗族的历史中实属罕见。是谁提出了组建兵工厂的建议?那几个外地的造枪技术工人的待遇,是高薪聘请,还是赠送土地?他们一共为民团造了多少枪支和手榴弹?这些细节都不得而知。
1950年7月威信解放后,陶家武装队伍解散,向政府上交了32支长枪和3支德国造手枪。
厚房的酒,与战争有关。
时光倒回到清咸丰七年(1857年)。
战争是一场残酷的相遇,除了生,就是死。陶三春与厚房第三代传人陶簸箕在太平天国运动中相遇了。
清咸丰元年(1851年),轰轰烈烈的反清太平天国运动爆发了。1857年,由贵州陶新春、陶三春率苗民起义军围攻镇雄州城,攻城未果,遂会同李开甲、卿蒲大、戚维新等反清武装共万余人移师威信,四处攻碉打寨,直指川南,路经双河,与陶簸箕相遇。
陶簸箕是陶一锁与陇氏小姐的孙子,从小聪颖灵活,练就了一身武艺,时常打抱不平、伸张正义,加上家业兴旺,被双河一带的苗族群众推举为苗族头人。陶三春路经双河时,陶簸箕为躲避征粮,带村民在洞口阻击。
“兄弟们,我们是一家人,我们是家门。”洞口对面,传来贵州苗民起义军首领陶三春的声音。
半晌,陶簸箕带领的村民们仍不松懈,战争蓄势待发。
“兄弟们,我是陶三春,我们苗家人不打苗家人。”对面,再次传来陶三春的声音。
无奈之下,陶三春派人掳走了厚房寨子里的一个姑娘,以人质为要挟停止了这场对弈。
第二天,陶簸箕带着骡子和酒去找陶三春议和并赎人。陶三春收下了酒,放了人。
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和丧权辱国,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让陶簸箕和陶三春同仇敌忾、一见如故。此后,陶簸箕更名为陶登春,率领自己的队伍加入了陶三春的起义军。陶簸箕所到之处,战功赫赫,赢得了起义军的信任和敬佩。从此,陶登春的名字便仅次于陶新春、陶三春了,他们被清政府贬称为“三大苗王”。后来,陶簸箕战死于四川叙永红岩洞。
这场相遇,陶三春和陶簸箕化敌为友。厚房的酒又香又烈,酒里有战火,酒里有生死相随的兄弟。
历史的车轮带走了厚房曾经的辉煌,天空的高远卷走了马蹄声、鼓号声、厮杀声、枪炮声,想必在每一个被触动的灵魂深处,这些声音依旧在耳边回荡。
城堡已破旧衰落,但厚房还有天然的小石林景观、生生不息的苗族文化。也许,它们同时被保护、被传承、被重视、被开发、被挖掘,当地的历史、文化、景观会获得另一种新生。
“……我们的责任,是把这些农事用具挖掘出来、抢救出来、记录下来、保护起来,把它们作为文化遗产,尽可能原汁原味原生态地请进这里,让其发挥认识历史的作用,让后人知道,原来我们曾是这个样子。抬头看历史符号,低头释故土乡愁,轻轻拾起,是为了不会忘记。”在威信县罗布镇簸火村丁家坝苗族文化博物馆里,展馆“前言”这样写道。
同样,在距离威信县80公里的镇雄县民族中学内,有一间30平方米的少数民族文化陈列室,里面摆设有彝族、苗族、白族的服饰、绣品、乐器、书籍等物品,还有一排排介绍少数民族文化的文化墙。课堂之外,学校开设有苗族传统手工刺绣课,课间开设民族舞蹈专场,镇雄县苗族文化传承人杨洪清是学校特邀的芦笙课指导教师。
学校与师生共同肩负起了民族文化传承的使命。而在镇雄县以古镇小米多村,彝族喀红呗的四位传承艺人张朝飞、张朝书、张朝文、卢军秀显得力不从心。他们平均年龄60多岁,诸如“打空翻”这类动作对他们来说,已经显得很吃力。村子里的彝族年轻人,要么外出打工,要么不愿意学。喀红呗团长张朝飞眉头深锁,若有所思。
《镇雄县苗族芦笙集》于2016年出版发行,它是镇雄县第一部用苗文简谱,汉字谐音收集、整理、出版的苗族芦笙曲作品,主编杨洪清为此付出了巨大的心血。唯一不足之处,是没有音频作品与书对应。对于几千年的苗族芦笙文化,此书既是传承,更是抢救。
赤水河畔的人们,都在用适合自己的方式,去记录一段段让他们遥不可及却又触手可及的岁月,去记录一个民族历经千难万险后重生的模样,去记录一条河的沧桑与欢腾,以及它欢喜时的微笑、它忧伤时的叹息、它滋养万物时的温柔之躯。(未完待续)

昭通日报全媒体记者 马燕 /文 通讯员 任正银/图 校对 彭小雨 沈艳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