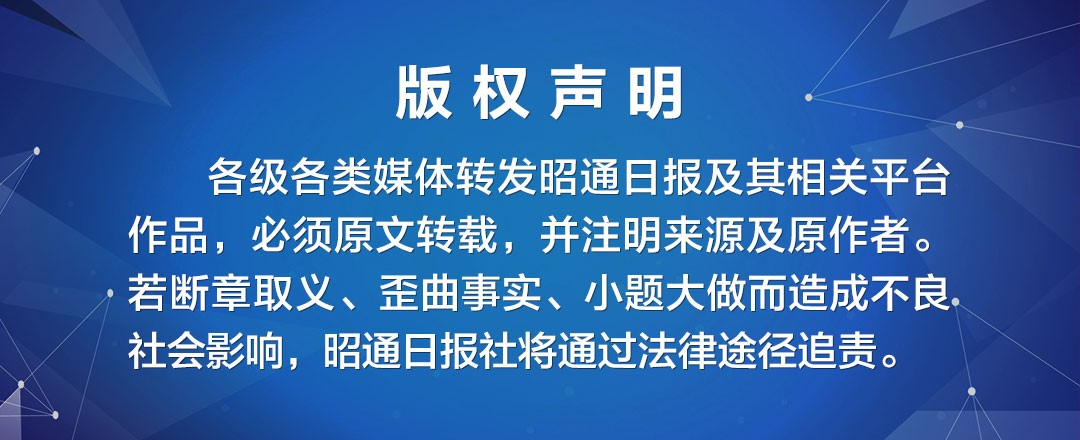2021-07-21 16:45 来源:昭通新闻网

我是故乡的孩子,也是文学的病人
——雷平阳在昭通谈诗人的故乡和精神的籍贯
今天回到故乡欧家营,应该说特别忐忑,近乡情怯是每个人基本的一个常态。回家,就像前往天空、前往乌有之乡一样。去年春节我没回来,一年后,家门口的那条河竟然清澈了许多,这是我特别特别意外的一件事。

广西云南作家评论家参观雷平阳旧居。
我在一篇散文里曾经写过,我大哥在父亲的坟头烧纸,妈妈就跟大哥开玩笑:烧这么多钱给他,他根本用不完,一定要让他把这些钱拿出一部分来,把这条河流清理干净。我当时就站在旁边,听到妈妈跟哥哥对话的时候,我觉得妈妈的幽默中有无奈,也有渴望。今天看见河道变清了,心里真的挺高兴。
我的高兴当然也跟大家的光临有关。我曾经在《广西文学》发表的长诗《昭鲁大河记》,写的就是这条河,并且它是我最偏爱的一首诗歌,因为它呈现了我少年时代的记忆、恐惧和慌张,以及没有安全感的生活,当然也有我的梦想,我想象中的故乡。诗歌中的很多事不是真的发生过,但是它曾经在我的梦境中出现,或者在自己偏安一隅的时候忽然访问过我。
我们的写作不一定非要去写发生过的,或者说看见的那些事件,更重要的是写我们内在之眼看见的,心里感受到的那些东西,那些不真实的,那些属于梦幻的东西。怎么把它们变现、让虚构、虚无、思想之物落到实处,一直是我写作的趣旨。我老家的房子被拆除了,代之的可能会是一座新屋(目前还没有),新则新矣,与之对应的精神供给以及乡村文化的堕落却是前所未有的,令人为之叹息。

广西云南作家评论家参观姜亮夫故居。
我曾经在很多年以前靠记忆把我的村庄画成一张地图,这是一张很大的地图——哪一家人住在哪儿,哪一家是几间房,哪些家居住在河流的两岸,一一精确无误。我觉得当年的那个村庄虽然跟现在的房屋质量不可比,但是每一次想到它是温暖的,它是金光闪闪的,仿佛总有无数的光在照耀它,现在的这个村庄虽然它变成了激进的、高大的、华丽的“天堂”,可有些时候我发现,住在里面的人,很多都变成了幽灵,遥远,不可知,没有亲切感。原先那些老房子,以及住在老房子里的人,是有温度的,真实的,你可以叫他叔叔,你可以叫他外公,叫他哥哥,叫她妹妹,但现在变成了统一、模糊不清的符号。村庄里,没有什么父亲、母亲了,也没有哥哥、弟弟和表妹了,仿佛所有的人都变成了一个,血缘、表情、思想、欲望,他们都是统一的,区别他们,只要用一个编号就可以。这种新生的恐惧和恐慌,导致所有归乡的道路,变得那么的艰难,不一样的道路似乎只通往同一个地方。我写过的一篇散文《霍俊明的忧伤》,写乡下人放阴,把自己的灵魂放出去漫游,有的灵魂结果再也不会归来。想想,现代游子的境况大抵如此。每一次回家都是一种困惑,都是一次探险,都是一次对记忆的检测。它带来的冲击和思考,我们每天都要面对,一些让人内心难安的东西已经成为日常。
即使你回了故乡,你想拥抱的人越来越少,有些时候拥抱一个人就是拥抱一件衣服,拥抱一个凳子。这带给我的慌乱,让人感觉你所难以想象的冷漠在现实中不处不在,那种超现实主义感,由不得你不将所有的人都看成“机器人”。面对现实,写作变得极其焦急,因为我们内心还有美,还有温度,还有光,还希望用笔创造一个世界。同时,我常常觉得自己创造的世界与现实生活一比较马上就变得很苍白,写作费尽了所有的心思,神的视角也好,天才也好,神助也好,一并出现在文字中,伟大作品产生的时候,现实往往很快就否定了它。当现实比你的文本更有力量的时候,我想是考察、考验一个作家的时候了。

广西云南作家评论家参观陡街。
上世纪90年代初,我离开昭通的时候,写过一首诗《出了昭通路就平了》。当时就想去这个世界闯荡,可世界何其壮阔,坐在汽车上,跑了一天还没跑出乌蒙山这颗泥丸的一半,而且多少年的一次次回望,愈发觉得小世界里存在着大世界,它的宇宙观,它古老秩序与法相,对应了我精神世界中没有边界的那片净土。我已经几年没出门,一个人尽可能地往内走,发现自己的内在目光。胸怀天下对我来说已经过去了,现在需要呈现的是内心那个世界,或者套用《发明故事的人》一书的书名的说法,我想自己给自己发明一个世界,自己给自己发明一点时间,自己给自己发明一点空气,自己给自己发明鲜花。昭通这片土地的温暖、情感,让自己的作品有灵魂和尊严,甚至有一双机灵的眼睛在背后盯着。重要的是,这片土地具有“发明”另一片土地的特质,它能满足我所有的非份之想。几年前我去往加勒比海地区的多米尼加访问,带给我一个惊心动魄的感受:读拉美作家的作品,都是从字面去看这些作品,但加勒比海之行,却能在拉美的土地上遇上一个个旧灵魂和新灵魂,原生文明与西方文明共同哺育岀来的一个“文明的孩子”是如此的与众不同,孤独而又丰饶。除了大海之外,其实它的整个自然生态与文化生态,跟云南何其相似。可那片土地产生了如此多的文学大师,令人由衷的敬佩!

广西云南作家评论家在辕门口参观。
生活中,我是一个极其枯燥、无聊的人,没有什么爱好,不会炒股,不打牌,聊天也聊得不好,随便跟人聊天,怎么把别人得罪了,自己都不知道,唯一的爱好就是近乎病态的写作。几年前,我出过一本关于昭通的书《乌蒙山记》,书写我个体经验和想象中的昭通。我不在意事情的真实性,我觉得最重要的是用你的美学方式去完成和重建某个真实。随着人工智能化,也许电脑比人说出来的格言还更像格言,还精细、还精彩,但个性化讲故事,人工智能可能完成不了,个性化的讲故事是暂时无法替代的。

广西云南作家评论家在雷平阳的旧居合影留念。
昭通是一个神灵游荡的高原,这片土地有无数双眼睛从天宫里面一直看着,我觉的他们也许是在监测我,而我也奉行“写作乃是写给神看”的法则,基于这一个契机,我想,也许我应该为这些天空里的人再写一本新书。
简介:

雷平阳,1966年生于云南昭通土城乡,现居昆明,供职于云南省文联、一级作家。著有《我的云南血统》《雷平阳诗选》《云南记》《基诺山》《乌蒙山记》《天上的日子》《悬崖上的沉默》《击壤歌》《袈裟与旧纸:雷平阳诗手稿》《送流水》等诗歌散文集。曾获《诗刊》华文青年诗人奖、人民文学诗歌奖、十月诗歌奖、华语文学大奖诗歌奖、鲁迅文学奖等奖项。

重返故乡:精神世界的拆毁与重构
——广西云南作家评论家昭通交流会发言暨雷平阳其人其诗评论精选

交流会现场。
霍俊明——《诗刊》副主编:
一个悖论的事实,雷平阳的“回乡”是以“离乡”为前提和代价的。雷平阳提供的是“大地伦理”受到挑战的精神背景和现实境遇,正如黑夜场景和废墟意象在他的诗行中频繁出现一样。当从病理式的症候阅读的角度出发,我们会在他的“故乡”“云南”看到世界主义景观的各种病症和暴力现场。雷平阳拒绝做一个乐观主义者,当然他也不是廉价的现实批判者,他的写作更像是在针尖上点蘸蜂蜜,在寓言、幻象、笔记体小说、田野考察和非虚构的综合想象力中展现了魔幻、怪诞的人性、存在以及世界本质。提醒一下读者,雷平阳不是一个地方主义的写作者,而是同时代诗人中少有的总体性诗人。他提供的“词条”既是见证、追挽和噬心的过程,也是词与物的较量,是精神世界一次次拆毁又一次次重构的求真意志的过程。
商 震——著名作家、诗人:
广西文艺评论家协会和《广西文学》编辑部和云南作家协会联合发起的“重返作家故乡”的活动,意义重大也深远。这个活动不是给功成名就的作家锦上添花,是重新审视作家成长的路程。这个活动对被探访的作家本人可能意义不大,但对研究者尤其是对正在从事写作的青年人有着很大意义。借鉴成功经验是青年人成长的必由之路。一个人或一件事的成功,都是有来由的。古人说,欲获某事成功,须得天时地利人和。雷平阳的家乡及旧居,从风水学上看,并无特别之处,甚至还有点欠缺。但是,古人说的天时地利人和,并不是具体到山形水势的样貌走向,就一定会出什么样的人。在文学创作上,当然也要讲天时地利人和,而在我看来,还要有神助。是如有神助的神,下笔如有神的神。雷平阳的心里是住着神的,所以笔下有神。他心里的神,是他的生活理想和文学信仰,是对现实生活的宽容与和解;是他多年阅读他人人生经验的独到总结。他的心里永远住着一个少年,一个不断对新事物好奇、探索、责问的少年。心里住着少年的作家,就永远在成长期。海德格尔说:归乡是诗人的天职。我认为,诗人归乡不是回到老家,而是从肉体到精神,是把从肉体生发出的灵魂再返回到肉体中去。许多人一生找不到自己的灵魂,许多人的灵魂再也回不到自己的肉身。我看到一些模仿雷平阳诗歌的青年人,他们可以把句式、结构、抒情手段学得很像,但是诗中的情感缺少来源和依据,主要原因是,雷平阳心里住着的神,他们没请到自己的心里。
桫 椤——河北作家协会文学院研究员:
昭通作为地理上的存在与我远隔千山万水,我对她具体的了解就来自雷平阳的诗和“昭通作家群”这个概念。因为疫情的原因,去年冬天我孤居在石家庄,每天必做的功课就是抄录雷平阳的诗,与诗里的大地山川和人事、与孤独的灵魂和深沉的思想对话。极难想象,昭通城乡接合部的欧家营作为雷平阳的精神原乡,在很早以前就能与遥远的我以及万千读者情感相通,这靠的是诗人的发现和建构:我在老屋和新居的对比中理解了他在诗中对尘世、故乡、传统和心灵世界的映射、阐释与重构。乌蒙山、利济河和五尺道不独属于雷平阳和昭通乃至云南的“地方”写作者,在他们的作品中,所谓“地方性”只是传统性和同一性的另一副面相。
唐春烨——广西评论家协会常务副主席:
就这样,你把我们带进了你的家乡:昭通,土城,欧家营。你告诉我们:村前的禾田是你母亲换在路边的;老屋是全村建在村东感受第一缕阳光的第一家;你曾花了很多时间绘制欧家营地图,地图里对应的是一个个你熟悉的“眼睛”,虽然目前“家乡已面目全非”;我们还见到了你的母亲,你的母亲微笑着坐在那里,睿智地看着忙碌的世界,接受着您儿子朋友们的合影请求,我们握着你母亲的手,好像握住了解开你诗歌密码的钥匙。是的,正是这“针尖上的蜂蜜 ”的品尝,让我们似乎抵达了雷平阳隐秘的精神腹地。读雷平阳的诗,总能让人读出一种挣扎及决绝,“让我站在你们的对立面/一片悬崖之上,向高远的天空/反复投上幽灵般的反对票”,这种挣扎及决绝,植根于这片古老的土地,这是对故土的深情感念,而这份感念,瞬间“带着整个世界软下去”。正是这份柔软,又给了诗人义无反顾的决绝,“给我子宫,给我乳房在灵魂上为我变性”“我祈盼这是一次轮回,让我也能用一生的爱和苦,把你养大成人。”
李 骞——云南省评论家协会副主席、云南民族大学教授:
雷平阳的灵魂与故乡欧家营的符号相融化并永恒相守。他在诗中把故乡符号的意涵提升到生存哲学的高度,故乡的符号不但超越了个体的意义,而且它的能指和所指都产生了新的内涵。如利济河、山、故乡植物、动物等符号都在形式上实现了第二次整合,而符号所暗示的内容,已经不能根据原始的表意来解释,而是要根据诗的审美理念去重新整理。也就是说,他诗歌中的故乡符号如同利济河的流水一样,所描写的不并是流水的自然意义,而是尘世生活中的人们强加给“流水”的人为的内在含义。接受者不能单纯地理解其故乡符号所表述的外在意义,而是要在符号原来的内涵的基础上进行扩充延伸,要寻觅物象的背景之外的内蕴。
黄佩华——广西民族大学驻校作家 硕士生导师:
作为昭通作家群的代表作家,雷平阳的创作始终植根于地域文化的土壤,沉浸在昭通这个具有浓郁地理环境特色氛围之中。他的地域文化表达形式独特且具独创性,文字清新脱俗,大气恢宏。可以说,是昭通的独特地理人文环境孕育和造就了雷平阳和昭通作家群。他们的成功为许多地域作家提供了样版和经验。
张柱林——广西评论家协会副主席 广西民族大学教授:
雷平阳诗歌与其说在书写和回忆故乡,不如说是在“想象故乡”,或在想象中“重返故乡”。他的诗中由此太彼、虚实相生、情景交融、无中生有、动静结合,层次丰富。仅以《杀狗的过程》为例,诗中至少包含三重视野:残忍(主人、屠夫)、愚忠(狗)与冷漠(旁观者)。但首句“这应该是杀狗的惟一方式”和尾句“说它像一个回家奔丧的游子”却又把一种叙事(诗歌能说是叙事吗?)伦理的凉薄呈现出来,并最终在一种“齐物”的视野中变成一种悲悯。当然我们确实能用“目的微不足道,过程就是一切”来解释,此诗主要在揭示人类的残忍。但“回家奔丧的游子”却不允许我们停步于此。
冯艳冰——广西评论家协会副主席 《广西文学》副主编:
家住土城乡,这世上还有什么能让雷平阳羡慕的呢?虽说有“出云南记”,但他什么时候离开过?尽管都是些“旧山水”,尽管他一程又一程地“送流水”,但更真切的是,他一次又一次地返回,是永远不变的“我的云南血统”。显而易见这没什么不好,对于云南——昭通——土城乡这样狭隘、偏执逐渐缩小的爱的过程,土城乡最后成就了他情感的冲击坑。进一步的探寻,我们知道这个过程不是机械单一的复制,而是由肉身的到达飞升至精神的回归。当我们回望他对土城乡针尖一样的爱时,实际上是“我住在大海上”的辽阔;重新审视他偏倚一隅对云南的凝视时,收获的却是“喜茫茫空阔无边”。由次第缩减的回归向无限空阔的出走,是雷平阳终其一生修行的功课,诗文是他精神的舍利子。有必要提醒的是,当我们阅读雷平阳作品的时候,我们隔着的并不是一个土城乡,一个昭通,一个云南,而是一个浩渺的天地。
李约热——《广西文学》副主编:
平阳是广西作家的好朋友,他在广西有很多的粉丝,这次我们广西作家、评论家来到他的家乡昭通市欧家营村探访,见到他的老母亲和弟弟,还有他昭通的好兄弟们,见到属于他的山川、河流和土地,他非凡的诗行后面,藏着玄机。可以这么说,平阳的诗句灿烂,平阳的人情温暖。
刘广雄——云南省作协原副主席:
现实总是狂飙突进或者随波逐流,一如雷平阳在行政区划及新版地图上消失的故园土城乡。雷平阳旧居残存的一间瓦房,以及近旁他的亲人正在兴建中的钢筋水泥小楼构成绝妙的隐喻。这个在语词与思想,故乡与异乡,生存与灵魂之间走钢丝的人,游走于都市与山野,向上建筑,往下掘井。雷平阳始终追求语言高度与思想深度的优美对称,就像雷平阳旧居旁那棵巨大的核桃树,根有多深,树冠就有多高。贮藏着六吨庙坝包谷酒的那间瓦房很快将荡然无存,那些酒必须远走他乡,最终进入雷平阳及其友人的肠胃,核桃树也很快将被连根拔起,连同新果和旧叶。田园将芜胡不归?雷平阳修灯送流水,端居诗歌庙堂,静观心花怒放,以笔招魂,挥毫返乡。
杨 昭——昭通学院教授:
故乡是地理性的,更是心理性的。是一个存在,更是一种思念;回故乡是一种行为,更是一种仪式,一种向来历,向人之初,向步履致敬的仪式。雷平阳这次返乡活动,对我们每个热爱文学的人来说都是一次确认自己灵魂构造的仪式,我们自己也该探探亲了。
杨荣昌——云南省委宣传部文艺处挂职副处长:
雷平阳的诗歌创作置身于生活的现场,真诚地唱出生命之歌,建构起开阔的抒情气场。云南的奇山异水历来是诗人吟咏的重点,也催生了无数的诗文佳作,人文与自然的交相辉映,构成这片高原之上的独特景观。他的诗歌《鲜花寺》,铺展开一幅云南的历史与人文画卷,展示了个人幽微的生存经验及破解当代人精神困境的求索努力,恰如其分的修辞效果和不懈的精神追问,诗歌气势浑厚,匠心独妙。
农为平 ——大理大学教授:
在当代诗坛,雷平阳始终是一个特立独行的存在。他从不追随任何一场语言狂欢,也不屑于取媚流俗大众,而是安静地“蜷缩”于云岭大地,用诗行垒砌一个充满泥土气息的诗性世界。这个世界的起点是欧家营、昭鲁大河、大山包,是金鼎山、澜沧江、基诺山……这些鲜明的地域符号使其诗歌中弥散着浓烈的南高原气息和挥之不去的乡愁,也是他与世界展开对话的根祇,从而形成了既小(地域)又大(世界)的言说空间,具有质朴、温暖的品格。以此为观照,雷平阳对现代化充满警惕,诗歌呈现歌咏荒野山水、自在生命,与抨击生态危机、道德崩塌两个鲜明向度,流露出某种逆流而上的悲壮意味。他执着奔走于偏远的茶林、庙宇甚至密支那,去挽留大地残存的诗意,努力建构一片生机盎然的“纸上旷野”。悲悯、敬畏、忧患,始终是其诗歌令人动容的精神内核。
房永明——广西作家协会秘书长:
四川盆地的暖流和云贵高原的寒流在这里相撞,形成了昭通特有的高原季风立体气候。雷平阳的诗应该是人间的冷暖相融、故土与都市相撞产生。从他的诗里,能读出音乐的节奏,人间的梦想,在这里,我们更能体会《亲人》的力量。雷平阳母亲在他父亲墓前,让儿子祈祷把门前的利济河变清,让我们真的看到了清清的利济河,或许这就是亲人的力量。让我们有更多的诗人,雷平阳一样的诗人,各种不同的诗人,让世界变得更加清爽。
荣 斌——广西影视艺术家协会副主席:
作为中国当代诗坛极具影响力的重要诗人,雷平阳从滇东北小城昭通走向全国,这既是他作为生命个体的一次孤独远旅,也可以说是当下整个昭通文坛的一次集体登场。与大多数优秀作家一样,雷平阳的创作一直和他脚下的这片故土密切关联。在他的作品中,字里行间都绕不开乡愁,绕不开那一座座土墙搭起的家园与村庄,更绕不开云贵高原的永恒色调:灰与蓝。他在贫瘠记忆的现实与物华天宝的背景的冲突交替中,既能昂头凝望明艳的山川大野,亦可垂眉低首关注晦涩卑微的命运。正如他作为一个诗人的性格:既隐忍、内敛、偶尔孤僻,也明朗、大气、偶尔张扬。恰恰是这些复杂而又简单的元素,形成了雷平阳独特的诗歌气质。
柏 桦——云南省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2010年冬,春城,我为《大地有多重》写书评,该书“楔子”,壮怀激烈,让念诵着“诚既勇兮又以武,终刚强兮不可凌。身既死兮神以灵,子魂魄兮为鬼雄”诗句长大的我血脉偾张,那是高天厚土无处安放的激昂与悲怆;2015年春,越南,亚太诗歌节暨世界文学大会,我常看到雷平阳远离地球村狂欢的人群,独踞一隅在手机上写诗,那些诗句,沉郁孤绝;2021年夏,昭通,我有幸见到雷平阳的母亲和弟弟,母亲慈祥的目光,弟弟憨厚的笑容,让我明白了故乡和亲人对雷平阳写作的意义。我想,不管雷平阳曾经或即将摘取多少文学勋章,当他回到钢筋混凝土的坚硬丛林,回到星星被城市霓虹灯遮蔽的漫漫长夜,能够温暖、慰藉、支撑他的,依然是故乡欧家营鲜美如初的芬芳回忆。

(昭通日报全媒体记者 杨明 毛利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