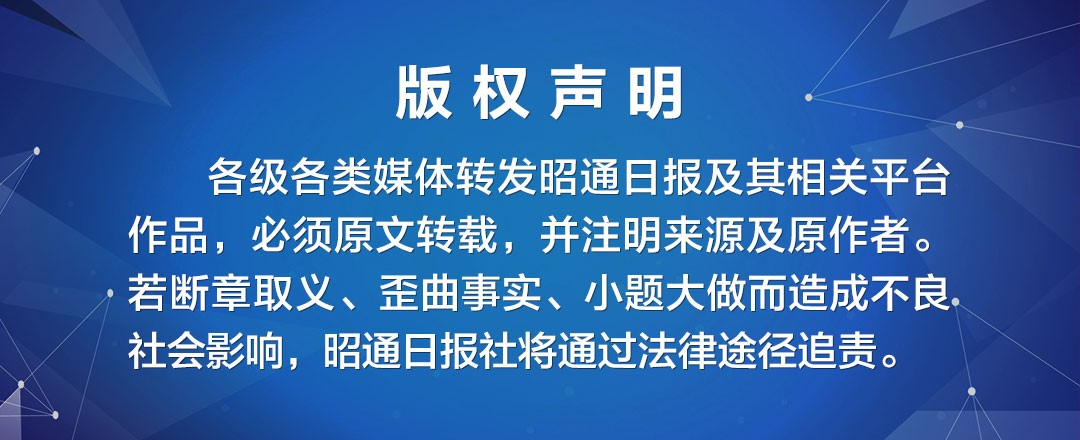2021-07-13 16:46 来源:昭通新闻网

人到中年,怀旧的心情就越来越重,常常想起老家那些枯萎的老树和去世的老人……
尤其是喜欢穿翻毛皮鞋的二叔。
在我记忆的反光镜里,二叔个头不高,经常穿一件中山装,胸前佩戴一枚“毛主席像章”。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爱憎分明,做事风风火火,说话掷地有声,是个急性子的人。二叔因儿子在林区当工人,总是能穿上一双底上钉有马掌的黄色翻毛皮鞋,经常“响当当”出现在村子里、田间地头、仓房前、晒场上。天长日久,人们都叫他“翻毛皮鞋”。
二叔虽然只读过高小,只认识半斗米的字,但在村里可算是个有文化的人。生产队那时,乡亲们就选他当了保管员,专门负责管理村里的粮食。一年到头,他的工作就是组织人把收上场的粮食晒、打、扬、簸、筛干净,然后该留种的留种,该上粮的上粮,该分给各家的分给各家,因而备受人们敬重。有时,生产队开会,或是分粮食,只要他脚下的翻毛皮鞋跺得咚咚响,嘈杂的会场便会鸦雀无声,分粮食的人们会有序地排起队,听他说话,随他安排。由于他做事公道,称粮食时,秤杆已经平了,他总会一边说“争生不争熟,人心不平秤心平”,一边随手抓几粒粮食添给你。因此,大家都认为他做事公道,就一直选他当保管员。
在村里人的眼里,二叔是个爱管闲事的“恶人”。在半饥半饱的年月,村里有饲养员去放牛时,顺手掰了集体地里的两包青包谷,被人发现,上报给二叔,二叔翻毛皮鞋跺得咚咚响,骂得饲养员狗血淋头,到秋收分粮时,硬是当众扣了饲养员家一公斤粮食。村里有位妇女从他手里称后领走一箩浸泡过农药的蚕豆去点种时,悄悄截留了一小碗下来,背地里拿到河里淘洗,准备拿回家当饭吃,被人举报。二叔认为一个人饿死都不该吃种粮,因此,也狠狠骂了那女的一顿,同样在分粮食时,也扣了她家一公斤粮充公。二叔的“恶”在村里出了名,谁家的孩子哭,父母只要吓唬:“翻毛皮鞋”来了,孩子就不哭了。正因为“恶 ”,所以,他在村里的威信越来越高,就连村里的狗遇上他,只要他跺跺脚,翻毛皮鞋咚咚地响,狗也会心惊胆战,逃之夭夭。
二叔的“恶”,我也曾领略过。有一年夏收时节,母亲去晒场上打蚕豆,我们几个小伙伴趁着二叔在仓库里睡午觉,借故去玩风柜,悄悄溜进了晒场。几位好心的大婶、大妈,分别往我们的衣袋、裤袋里塞蚕豆,催我们赶快回家。恰在这时,二叔不知从哪儿冒出来,口里一边喊着:“是哪家的娃娃来偷大集体的蚕豆,宰掉他的手……”一边朝我们跑来。听到翻毛皮鞋“咚咚咚”的响声,我们一个个迅速把口袋翻出来,将蚕豆哗啦啦倒回了晒场。我们几个娃娃勾着头,像木桩似的站成一排,接受二叔的训斥。骂过之后,二叔却抓起一些蚕豆分别塞给我们:“莫哭了!莫哭了,小娃娃不懂事,这是集体的粮食,不是我家的,以后不准来啦……”
在家乡巴掌大的天空下,二叔是村里为数不多的几名共产党员之一,不仅当过生产队的保管员,还当过记分员、会计、队长,算是我们家祖辈最大的“官”。因而,村里不论红白喜事、赡养父母、家庭不和、邻里纠纷、牛吃庄稼、马踏田地等,大事小事,都少不了二叔。好事请他主持,坏事请他摆平,矛盾请他化解。在乡亲们的眼里,二叔是个响当当的人物,他也是我从小最敬佩的人。
二叔经常用“人有三穷三富,马有九瘦九肥”这句话叙述家史:在我爷爷辈上,家里养着几匹大骡子,煮着一灶酒,驮到狗街、猫街、马街、黑井卖,在村里是数一数二的富人家。由于家境宽裕,爷爷奶奶从小就对是长子的父亲娇生惯养,百般宠爱放纵,使得父亲十多岁就吸上了鸦片,成天不干活,摇骰子赌博,养成了好吃懒做的恶习,还经常偷家里的东西变卖换鸦片吸。结婚以后,娶进门的女人管不住父亲,还经常挨父亲打骂,不到一年,身怀有孕的女人就吊脖子死了。后来,出身贫寒的母亲,由父母包办,在别人的撮合下,不幸踩入了婚姻的陷阱,堂堂一个大姑娘,被“二婚”的父亲娶进了家。
母亲来后几年,相继有了大哥、大姐。可已为人父的父亲还是恶习不改、不务正业,偷偷摸摸吸鸦片,摇骰子赌博。好在有爷爷奶奶庇护母亲,日子才在酸酸甜甜中勉强过着。没过几年,爷爷奶奶相继去世,母亲管不住父亲,厚厚的家底,就像放回水里的冰块返本还原,被父亲“坐吃山空”了。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家被划为贫下中农。和全村人一样,要养家糊口,必须靠挣工分才能分粮、分红(钱)。由于国家禁止吸鸦片,父亲黄皮寡瘦,像个病人,干不了重活,挣不到高工分,只能当放牛的饲养员。于是,本来柔弱的母亲,似小孩子般过早地挑起大人的担子,背起大人的包袱,不得不当顶梁柱,支撑起了全家人生存的大厦。
母亲毕竟是个女人,整天起早贪黑地干活,脚不点地地奔波,始终很难扭转家庭的困窘,还常常挨父亲打骂,便提出要离婚。母亲越这样要求,父亲骂声越大,拳头越重。二叔看不下去了,跑过来我家,翻毛皮鞋跺得咚咚响,先是臭骂父亲:“大哥你吃粮不管闲事,还打人骂人,你手摸良心想想,像大嫂这样点着火把都找不到的女人哪里有,有本事来骂我、打我嘛……”
父亲自知屁股里有屎,败下阵来,走开了。二叔又转过身来劝慰母亲:“大嫂,都是我大哥的错,你现在靠不住他,以后可以靠儿女过。孩子都大了,我会批评大哥改邪归正,莫离了,莫离了……”母亲在二叔的劝说下,又只好抹抹眼泪,苦苦地维持着全家人的生活。
母亲是个不幸的人,如山羊逃不脱狼贪婪的目光,小鸡逃不脱老鹰的魔爪一样,时时都面临着父亲的威胁。二叔对父亲的“批评教育”过一段时间就不管用了,父亲又借酒发疯,开始打骂母亲,还胡说母亲与二叔私通,要杀了母亲。二叔听到吵架声,手拿钳子跑过来,翻毛皮鞋跺得咚咚响地教训父亲:“大哥,你‘嚼牙巴骨’呢,今天我就摘了你的门牙。好好一个家,被你搞得乌烟瘴气的……”
父亲自知理亏,见二叔脚下的翻毛皮鞋跺得冒火星要动真格,耷拉着脑袋跪在地上:“二兄弟,我错了,我说的是醉话,以后我改……以后我改……”接着,二叔又转过话题劝说母亲:“大嫂,人正不怕影子歪,只要我在,大哥不敢动你半根毫毛,既然他已认错,毛主席都说知错就改,就是好同志,莫闹了!莫闹了……”母亲又一次抹抹眼泪,梦想着走出黑暗就是黎明,仍苦苦地维系着全家人的生活。
母亲的婚姻是悲哀的。与父亲阴差阳错地结合,根本就没有享受过什么叫爱情,如同关在一厩的驴和马、牛和羊、鸡和猪,雄性总是强悍地占有懦弱的雌性,让雌性无奈地怀孕 、产子、下蛋、哺育。大哥、二哥、三哥、大姐、二姐和我,就是这样来到人间的,像群跟着母鸡刨食的小鸡,风里来、雨里去,在母亲的翅膀呵护下长大。家里的油盐柴米、穿衣吃饭、病痛冷暖、上学读书、结婚娶嫁,一切事务全都落在了母亲的身上。而当母亲把自己的亲生骨肉含辛茹苦地养大之后,对于她来说,面临的可能是被遗弃。
我九岁那年,哥哥姐姐们娶的娶、嫁的嫁,都有了儿女,婆媳妯娌之间的摩擦越来越多。在二叔的主持下,原来的大家庭分成几家,各立门户,我和母亲拥有几样破旧的家具和一间低矮昏暗的小屋,构成了人生的第一个“家”。父亲没人要,单人独户一家。而父亲却常来骚扰我和母亲。二叔依然会跑来,翻毛皮鞋跺得咚咚响,像个长辈似的教训父亲:“大嫂的筷子又没担在你碗边上,脚都伸进棺材半截的人了,还死不悔改……”依然不停地安慰母亲:“俗话说树大分桠,儿大分家,大嫂你把这些娃娃拉扯成人,不简单了,就剩小六这个儿子,只要有我在,兄弟会帮你呢……”母亲依然抹着眼泪,百折不挠地领着我苦苦地生活着。
母亲是个苦命的女人。如一只在深山老林里十字路口走错路的羊,一路奔波,一直寻找,始终走不出人生那片遮天蔽日的密林,苦苦挣扎着、拉扯着我们长大。转眼,已从鲜艳的桃花变成了干枯的老树。我十三四岁时,她已接近六十岁,青春的憧憬被岁月的年轮碾压成灰烬,也如那些被山风吹落的树叶,飘得很远、很远。可在我的心里,母亲始终是一株霜雪冻不坏的庄稼、一块无私奉献的土地、一棵火烧不死的芭蕉、一株割不绝的韭菜、一池挑不干的井水,顽强地走在人生的沼泽地上,不停地跋涉,不停地寻找着人生的幸福彼岸,不是为自己活着,而是为了我的存在而痛苦地活着。
年幼无知的我,却让母亲操碎了心。因为不懂事,有时肚子饿,偷吃人家的水果、包谷、红薯、蕃茄、青笋,或是捞鱼摸虾、捕雀打鸟,或是跟别家的孩子顶嘴打架,常有人跑上门来论理讨说法,索要赔偿,惹得母亲用棍棒、扫把追着教训我。听到我的哭声,二叔总会跑来劝母亲:“大嫂,娃娃不懂事,偷点东西吃不犯法,打伤了,有个三长两短不好,以后我来教育他,莫打了!莫打了……”好几次,二叔穿着翻毛皮鞋的脚步声,总是让我免受了很多皮肉之苦。
最难忘的是那年夏天,我们一群娃娃在去找猪草的路上,路过一道小水坝,看见泡田栽秧的水快放干了,已接近坝底,并有鱼不时浮出水面,在我这个“娃娃头”的指挥下,一群娃娃赤裸裸地像鸭子,扑进水里,追逐嬉戏,用篮子“撮鱼”。因水浅,几个回合,水就被我们搅成泥浆,一条大鱼被追得筋疲力尽,撮到了手。爬上岸,我们猫玩老鼠似的在草坪上你摸我捏,惊喜了半天,正商量着把死去的鱼偷偷拿回家“打牙祭”。此刻,生产队的放水管理员不知从哪儿冒出来了,肩上的锄头往我们面前“哐”地一放,又骂又吼:“你几个小短命鬼,谁叫你们来偷大集体的鱼?这是破坏社会主义,斗死你们……”
一阵刑讯逼供似的审问,吓得我满裤裆地尿,只好低头认错。我们一个个比麂子还跑得快,溜回了家。我惶恐地躲进了二叔家的牛厩楼上,像只被猎狗追捕的兔子,蜷缩在草堆里,不敢动弹。
傍晚,我“领导”的“偷鱼事件”如决堤的水,在村里传开。透过草楼的窗缝,我看见放水管理员正在举着那条大鱼,站在晒场上,开会似的围拢来很多人,大家议论纷纷,斥责我们的罪过,有的说要批判家长,教育娃娃;有的说要加倍罚款,矛头都指向我。身为生产队长的二叔却从人群中站了出来,对着众人说:“娃娃不懂事,既然已经犯了,该罚就罚,集体的财产不能破坏,确实该教育的要教育。”听话听音,乡亲们看在二叔的面上,同意罚我家八角钱。只见母亲哭着下跪,向乡亲们认了错,为我交了罚款,便羞愧地跑回家,拿着棍子呼唤着我的乳名,到处找我。我只有哭泣,不敢答应,不敢露面。
透过窗缝,我还看见那条大鱼被乡亲们摸来摸去,个个都想吃,却出不上队委会定的价,最后还是二叔出了两块钱买回了家。
我听到二叔刮鱼鳞、洗鱼、剖鱼肚的声音,之后不久,鱼的香味也由远而近地朝草楼飘来。
透过窗缝,我还看见二叔端着牛料从牛厩走来,翻毛皮鞋的声音离我越来越近。喂完牛料,二叔上楼来拿牛草,无意中发现了哭哭啼啼的我:“小六啊小六,你妈到处找你呢,下来!下来!”
听到二叔喊我,母亲也知道了,拿着棍子,喊着我的乳名,骂着跑来。我急中生智,一把抱住了二叔的腿,躲在二叔背后,恨不得变成一条蚂蟥紧贴在翻毛皮鞋上,让母亲无计可施。二叔一边劝母亲,一边叫我认错,我哭哭啼啼讲了事情发生的经过,又软口软舌地认了错,才逃过一难。平息了“偷鱼风波”,二叔把我和母亲叫去吃饭,让我尝到了一口鱼汤、一块鱼肉。那鱼肉、鱼汤一直在我腹中,多少年没有被消化似的香到现在。
二叔家和我家仅一墙之隔,听得见两家人说话,闻得见两家的饭菜香,有好吃的,二叔总会匀出一点叫我去拿。所以,我最喜欢去二叔家玩。二叔还是重复着那句老话:“人有三穷三富,马有九瘦九肥,腌菜罐总会有发水的时候……”有时,看见他洗脚换下了那双翻毛皮鞋,我好奇地把脚放进去。二叔笑笑:“咦,小蚂蚁穿大皮鞋。”并不断地鼓励我:“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你一定要好好读书,将来像我一样当‘大官’,穿翻毛皮鞋……”
二叔爱看书,看的都是烟盒大的《毛主席语录》,砖头厚的《毛泽东著作》等红色书。时不时还领着我念上几段,或叫我们背几句,他教育我时也几乎是引用《毛主席语录》里的话。二叔“当官”时也关照过我家不少,比如让父亲放牛,让母亲到晒场上打粮,让我家享受贫困户的救济,使我有衣穿、有饭吃,我一直像二叔手下饲养的小猪小牛,健康地成长着。
20世纪80年代我参加工作以后,也模仿二叔买了一双翻毛皮鞋穿上,很多人讥笑我是“土包子”。第一年回家过春节,我给父亲和二叔各买了一双翻毛皮鞋,二叔竖起大拇指夸我“有孝心”。
过了两年,父亲去世。每年上坟,二叔总要带着我去父亲的坟前祭奠,跪在父亲的坟前祈祷:“大哥!大哥!起来吃饭喽,今天小六和我来看你,你在阴间一定要好好保举小六,将功补过……”
每次回老家,见到年岁已高、腰弓背驼的二叔,脚下的翻毛皮鞋声音已不是那么清脆,可满头白发的二叔总忘不了问我母亲的情况,再三叮嘱我,要好好善待母亲:“你妈一生命苦,没过上好日子,现在熬出头了,你要好好对待她,让她多享几年福。”
当我把一双翻毛皮鞋,或是水果、糖果送给二叔时,他总是拒绝:“你在外面紧,要买房子,要供娃娃读书,还要养你妈,小六啊小六,我空脚白手没东西给你,全家都享你的福,以后莫拿回来了!莫拿回来了……”
令我遗憾的是,自己还来不及报答二叔,他就走向了“另一个世界”。那天,我在国外出差,接到二叔去世的电话,恨不能包机返程。那一次欧美之行,本来是件很愉快的事,却成了我揪心的苦旅。回来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我为生前没有带二叔到楚雄、昆明转转,或是来城里和我生活一段时间,让他也沾沾我的光,听他讲讲《毛主席语录》而深感内疚。
直到现在我才发现,在我心灵高处站着两个人,一位是母亲,一位是二叔。是二叔拉开了我心灵的窗帘,让我看到了人生的阳光;是二叔还给了我丢失的钥匙,让我开启幸福的大门。总想着要为二叔做点什么。想来想去,我只好按照乡俗,把二叔的坟修筑得比祖辈的高些,然后,在二叔的坟前放了一双崭新的翻毛皮鞋。

作者 李光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