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新闻 2021-05-25 09:09 来源:昭通作家
”
罗剑宁,昭通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在读学生。
”
嵌入骨缝里的乡土
罗剑宁
一
柳光先是一个石匠,也是一个小说家。
他打磨一生,才写好处女作的结尾。“显考柳公光先之墓”。句短意长,字字千钧。他把自己摁进小说,变成一个句号,摊开在这茫茫人世,任人阅读。可他从来没有遇到一个忠实的读者,秋风荒草里,只有麻雀偶尔聒躁。
我是一个奇怪的人,时不时会去山上翻开他。
正月初三,我又去山上,看到他辛苦一生的结尾,被石头砸掉了一个角。石头是从观音岩上掉下来的,或许是观音,或许不是。我想,定是上天对他的结尾不满意,要重写一个开放式结局,让他的后人世世代代接着写。
下山遇到他的儿子柳昌财,生活侵蚀,脸上风化出条条沟壑,细看,里面还有点点尘土,在未来的某一天,土里将长出植物。他给我装烟,我没有要。为了不重复父亲的命运,他选择了做个木匠。大半生为村里人打桌子、打板凳、打柜子、打床、打棺材…我告诉他山上的事,他没有回答我,只说自己年纪大了,干活时越来越分不清,打的是床还是棺材。
二
时隔一年,我又重回到老房子里。
晚上做梦,梦到祖母在做梦,梦中有母亲、父亲和哥哥。
母亲从墙上的相框里面走出来,缝缝补补一些零碎的东西,脖子上牛角撞出的血洞,神秘幽深。她不小心从板凳上摔倒在地下,破碎成一地的打碗碗花。
父亲迷路在山里,还没有走出来。他的柴刀已经生锈,锈到只剩下手中那个刀把。满山的竹林摇摇摆摆,父亲草木皆兵,四处逃窜。
哥哥走到悬崖边上,望着天上的月亮傻笑。他还是一个四岁的孩子,肚子还是在痛。
祖母佝偻在床上,被子没有盖严实,浑身颤抖。我轻唤一声,祖母醒来,她到处寻找,可房子里只有她一个人。
她烧开水淋簸箕为我们招魂,母亲回来了,父亲回来了,哥哥回来了,只有我没回来。我喊他们,喊他们找我,喊到声嘶力竭,喊到梦醒。
老房子里还是只有我一个人。睡不着了,开着手机手电筒出门,去祖母坟前。
祖母坟前的车前草生长茂盛,它们颗颗都含着泪,它们做着多子多福的梦,它们就是我的祖母。
黎明的风吹得一地的草叶齐刷刷地指向我,我想梦里,祖母终于招到了我的魂。
三
祖母死后,我偷偷找人算命。
找到一个老道士,他满脸粗硬的胡须,像冬风刮过的森林。
老道士翻开一本书,开始推算。他手里世代传承的命运,已泛黄残缺。隔上几页,有的人生皱皱巴巴,满是油污,不知那一群人,会被写在上面。
他推算完告诉我,我的前世是一个凶残的刽子手。我前世造下的孽,都将在今生一并偿还。我前世砍向别人脖颈的刀,都将在今生一一砍回来。
原来如此,家里人死的只剩下我,是我在还前世的账。可那些本该砍向我的刀,为何次次砍错了人?还是它们清楚的知道,那里才是我的软肋。
四
楼上又传来了响声。
我赶紧躲进被子。祖母告诉过我,晚上楼上如果有响声,就是有死人在收脚印。人死后,要把生前留下的脚印一个一个的全部收起来,然后才能去投胎。
每次听到楼上有响声,我都会为祖母庆幸,为父亲担心。
祖母一生到过最远的地方是长安镇的集市,离家只有十四里。可父亲一生到过最远的地方是北京,走了那么多年,也不知他是否收回了那些遥远的脚印。
我没有父亲的勇气,二十年来,从不敢走远。
我总害怕自己,将来会因为遗忘了某个脚印,而失去重新做人的机会,变成一只不入轮回的鬼。
五
一把扫帚和一把铁铲,加上他,便是两个老环卫工。
这个老人在环北路上打扫了多年,眉间的愁苦和头上的雪色却始终也扫不净。
行人们从不和他交谈,只有环北路和他相依为命。每天他都认真的打扫,脚步蹒跚。命运里遍生骨刺,人生整个颠簸。
清明节回老家,我见过一次他。
那天他红着眼眶,把满地的落叶废纸仔细地扫入垃圾桶,似乎还把自己也倒了进去。离得太远了,我不敢确定。
我走的时候,他正在追逐一个被风卷起的黑色塑料袋。那着急的样子,像是在追逐早年的自己,或者另外一些回忆。
六
听老人们说,南乡坟在民国时是一个乱葬岗。后来破四旧时,铲掉了茂盛的坟墓,改种了庄稼。后来分给了我家。
父亲在南乡坟种苞谷,刨个坑,把苞谷种丢进去,丰收。种了几十年,误把自己也丢进了坑中,结出一个半人高的小石堆。
小石堆躲在荆棘和荒草丛中,畏畏缩缩,欲露不敢露,像极了父亲生前躲在人群里的样子。也许风吹草动稍微大点,父亲就会趁草色潜逃得更远。
日日风吹雨淋,小石堆裂开了几条缝。时常有人告诉我,晚上路过时,会听到缝里挤出父亲的声音,喝得醉醺醺的,满嘴胡话。
听得多了,我也决定去看看。
一天借着黄昏去南乡坟,等着父亲说话。等到半夜,也没有听到半点动静。只有荆棘丛生的坟头上,几株玉米高举着红穗子,似在窃窃私语。
它们耕种了父亲一生,如今仍在劳作。
七
王富如是一个民间画师,是我舅公。
贫穷、流浪和孤独,是他的自画像,虽显潦草,却笔笔精准。
他用一生画了一个圆:昭通、昆明、红河、文山、保山、文山、红河、昆明、昭通。一个圆,把大半个云南和大半个王富如圈禁其中。剩下的小半个云南,在王富如的脚步之外,剩下的小半个王富如,在云南之外――在毕节,前妻的墓中。
套在骨缝里的犁,让他不停流浪,去耕种一片世代贫瘠的土地,幸福总是歉收,悲伤总是满仓。
素描的一生,像从故乡流出的白水江,每一段,都有不同的籍贯和坎坷。
八
时间未曾动过恻隐之心。抬大伯上山后,所有人又老了几分。独自在坡上发呆,回味亲戚们对大伯的哭别。
锣鼓依旧喧嚣,盖棺尚未定论。
秋草无边,群山老枯。
想到将来自己躺在盒子里,人们向我告别时,装我的盒子,会不会向我道一声:久仰。
九
沙坪头,是我的家乡。是一块又一块的山坡,像补丁一般,被缝补在山上。
山坡上的人,和泥土是一个颜色,和泥土是一种命运。山坡上的坟,比山坡上的房更多,房又比人更多。一年四季,佝偻的老人耕种着土地,惨淡经营着残年。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花朵和夕阳都与他们无关。满眼迷茫的小孩子,甩着鼻涕去上学,又甩着鼻涕回来,割猪草、放牛,看草盛豆苗稀,等待月荷锄归的爷爷或奶奶。
山坡上的人对土地恨之入骨又爱之入骨,一平米土地,便可导致两个家族几十年的仇恨。即使是亲兄弟,也会在堂屋中间挖条沟,老死不相往来。然而大部分人并没有机会老死,各种病痛会提前赦免他们。
每年,土地和人,相互耕种,相互收获,相互沉默,无止尽的循环着,世世代代无穷尽矣。
劳动节回家,在潮湿的公路上,散落着许多纸钱,我知道,沉默的土地,又收获了一茬人。
 来源:昭通作家
来源:昭通作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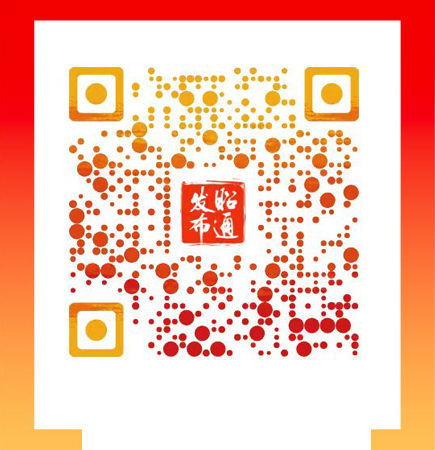

联系电话:0870-2158276
登报作废:0870-3191969
联系邮箱:ztnews@163.com
主办:中共昭通市委宣传部、市政府新闻办;承办:昭通日报社;Copyright © 2017-2028 昭通报业有限责任公司
新闻爆料、涉未成年人举报、涉毒及有害信息举报:0870-3191933 举报邮箱:ztnews@163.com,涉毒举报,疫情求助
登报作废:0870-3191969,流量造假、黑公关、网络水军举报电话:0870-2159980
昭通市“打假治敲”举报电话:0870-2132590,举报邮箱:305906736@qq.com,举报地址:昭通市昭阳区公园路45号市委宣传部(市委大院内)
滇ICP备19003243号-3 ;云南省公安厅备案号:53060203202019;互联网信息新闻许可证编号:53120180014;互联网出版许可证:(总)网出证(云)字第002号
本网站法律顾问——云南意衡律师事务所 赵文律师,未经昭通新闻网书面特别授权,请勿转载或建立镜像,违者依法必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