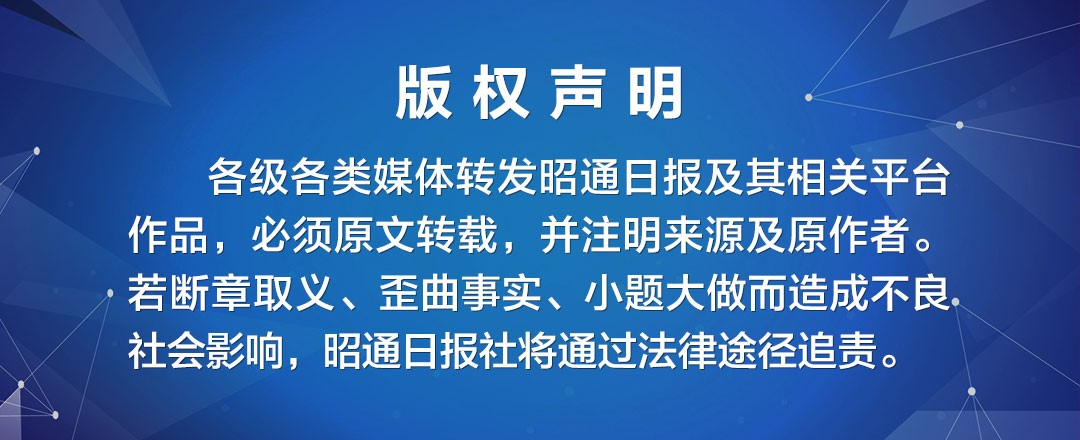2021-03-24 09:52 来源:昭通新闻网


蒋仲文 回族,昭通市昭阳区人,曾是云南省文联委员、云南省作协理事,多年任昭通市文联副主席、作家协会和剧作家协会主席。他的作品有小说、散文、话剧、诗剧、电视剧、文艺评论等。他曾获得过中央电视台电视剧创作二等奖,两次获得云南省文学艺术政府奖,两次获云南省新剧目展演编剧奖。目前已退休,居住在昆明市。
星期天,上午八时许,麦子踏着春天明媚的阳光,走在都市的大街上。她那一米七的个儿,健美的腰身曲线分明。那修长的四肢,健康而匀称,浅褐色的皮肤闪动着阳光轻抚麦浪的光亮。她步履从容,款款而行,脸上不时漾起抑制不住的笑意,身上裹挟着泥土的气息、山野的清风,在人群中,凸显着不一样的气韵,和那些婀娜多姿的都市女孩相比,很容易让人区分开来。
同样是人头攒动,熙来攘往,同样是抛置在人潮中沉沉浮浮,这里和乡场上的情景却大不一样。这里的人是陌生的,神情也是陌生的,冷着脸,脚步匆匆,互不相干,都想尽快脱身,从无奈捆绑的桎梏中挣脱出来,逃离而去。而乡场上人们的脚步是从容、悠闲而耐心的,充满信心和希望,充满期待和好奇。偶尔会遇到一位多年不见的人,脸上就花儿般绽放出喜悦,拉着手问这问那,毫无顾忌地扯开嗓子畅快地笑。有时,遇到邻村儿时的同学,就惊喜得忘乎所以,缠在一起久久不愿离开。居住乡村的人那残留在泥土深处的文化的根脉,虽同样经受了滚滚红尘的洗涤,仍顽强地植根在内心深处。越是残留的越是根深蒂固。那远古的呼唤和祖先的嘱托,伴着山风和松涛,伴着悠远古道上的马蹄声、鼓点和筝乐,涌动而至,让人心潮澎湃。
昨天晚饭后,麦子接到了未婚夫石松的电话,说晚上要开股东会,研究几个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估计要开到很晚,会后他就不给她打电话了,不影响她睡觉。他要麦子今天早晨到他住处去。他毫不掩饰想见到她的急迫心情。麦子挂了电话,甜甜地笑了。
麦子到石松住的别墅区,有二十公里,那儿已是城乡接合部。那住处十分气派,属全国十大别墅群,住的多是城市的“新贵”。麦子到那里,得先坐公交车,再换乘地铁,需要一个多小时。本来,石松要叫他的驾驶员开车来接她,她拒绝了。她不想弄得兴师动众,也不想在石松的公司公开她和石松的关系,至少婚前还想保住这点儿“秘密”。她感到,幸福来得太快,她还没有做好接纳的心理准备。
麦子终于从拥挤的人流中分离开来,走进了一条僻静的小街。时间好像一下子慢了下来,麦子的心境也随之松驰了下来,她感到身上舒服了许多。
麦子上了K路小公交车。这车只有七个座位,是因为这条街行人稀少而专门开通的。走在街上的,大多是到菜市场上买菜的老人,他们步履蹒跚,举步缓慢。不时还可看到相互搀扶着的老夫妻,麦子心里暖暖的。
挨着麦子座位的,是一对老夫妻,大约七十多岁。男的满头白发,体弱清瘦,身子佝偻。女的紧挨他后面,中等身材,体态匀称,鹤发童颜,精神矍铄。她身旁立着一辆专门上街买菜的小推车。一看就知道,不管是上街还是在家里,一定是女的照顾男的。也许她到街上买菜,无需老伴一起去,帮不了她做点什么,只是为了敦促他一起出去走走,活动一下筋骨。到了耄耋之年,为什么多数是女的比男的健康、还承担起了照顾男老伴的任务呢?
细细观察,这路公交车的服务特点颇多:车子行进得慢,站与站间的路程短,停车时间稍长,停车和车子启动较慢;有时遇到行动迟缓、上下车费力的老人,驾驶员就耐心地等待着。总之,处处体现出文明、礼貌的风格,让人感到温暖。
到了一个站,那两位老人站起身来准备下车,女老人左手提起买菜的小车,伸出右手搀扶着老伴,挪步向后门走去。麦子忙起身,从老奶奶手里接过小推车,伸出右手搀扶着老爷爷。两老人看了麦子一眼,脸上露出慈祥的笑容,眼里盈满感激之情,连连说了两声:“谢谢!谢谢!”。
车子缓缓启动时,麦子想起了小时候经历过的一个场景。
那年麦子十三岁,小学毕业了。深秋时节,父亲托人在供销社买了两袋化肥,连着家里的一袋大米、一腿牛肉、一罐牛油、一袋洋芋、一些瓜果什么的,装了满满一牛车,要送到大舅家去。因为外婆住在大舅家,每年父亲都要用牛车给他们送去一些吃的和用的。每次去,麦子就坐在牛车上,一起去看望外婆。
那天早晨,牛车沿着长长的坡路,吃力地蜿蜒而行。这段路程,让人感到有些沉闷。过了好长时间,终于摆脱了山路的纠缠,眼前豁然开朗,面前呈现出一片一望元际的麦田。麦子已成熟,正等待着盈满喜悦的开镰。父亲精神为之一振,深情地品咂着这幅金色的画卷,不舍急于离去。他搁置了牛鞭,任牛车顺车辙缓慢地行走,像一条小船在金色的海洋里自由地游弋。这憾人心旌的画面,要是在城里人的眼前,也许只是一幅赏心悦目的图画,但在村里人的眼里,却赋予了它极为丰富、深情的内涵,因为与自己的生存息息相关,和堆放在楼上粮食的多少息息相关,而此时呢,却与这辆负重的牛车上拉着东西的多少息息相关。遇到丰收年,麦子他们家送给外婆的,不仅有粮食,还有牛肉、牛油等更多的东西。这车上承载的,是乡下人沉沉的喜悦、孝心和自豪啊!
随着牛车的行进,父亲脸上的喜悦也在一点点添加。这时,父亲突然亮开嗓子,吼起了山歌——
前面有座岩,
请个石匠来。
拦腰凿个洞,
放出清风来。
(注:这是作者在永善县收集到的一首民歌。在当地,这样的歌谣俯首皆是。)
歌声里充满了欢乐、自豪,充满了迎着艰难迈步向前的信心和勇气。
麦子下了小公交车,转上一条宽阔的大街。
麦子大学毕业后,把户口落在了这座充满诱惑的城市。两年过去了,她依然在努力地接近它,融入它。原本,她可以接受石松的安排,到他公司任职的,这是一条便捷、安稳的路,但她毫不犹豫地拒绝了。她认为,这会让她难以摆脱对石松的依赖。她想,这可能会遇到诸多阻碍她独立人格形成的事。她经过自己的努力,终于在一家大公司找到了工作,并依然隐瞒她是“已很有名气”的石松的未婚妻这一事实。一切都得靠自己,她想。石松不也是这样走过来的吗?
麦子和石松在同一个村子里长大,石松大她七岁。两年前,石松开始追求麦子时,她刚大学毕业,而他已在城里打拼了六年,事业上已小有成就。开始,麦子奇怪,城里有那么多漂亮的女孩,他为什么不动心,却偏偏爱上了她,且爱得那样专一、深情、真诚?渐渐地,她似乎找到了石松那深藏在内心的秘密。十二年前,麦子还是一个读初中的小女孩时,石松就暗恋上了她。那时,他就许下了心愿,一定要做出一番事业,靠自己的真诚和能力,赢得麦子的芳心。这种从深山厚土里长出的爱的“叶芽”,从大地里汲取了无限养分,虽经历了种种艰难困苦、风刀霜剑的洗礼,却更深沉纯净。正是这种厚土里长出来的爱,感动了麦子。她终于明白了,石松对她的深爱,是和那片生他养他的热土相依相存的。
那天,父亲驾的牛车到了外婆家后,外婆就忙着宰鸡,叫大舅切下一块牛肉,拿出鸡蛋,做了一桌子的菜,像过节一样丰盛。那一夜,父亲和大舅有说不完的话,他们边喝茶边聊天,直到深夜。麦子和外婆在床上都睡醒一觉了,还听到他们在堂屋里说话。
麦子十分喜爱外婆,珍爱和外婆同床共枕的每个晚上。外婆把麦子搂在怀里,不停地问这问那:爷爷的病好些了吗?地里的庄稼长得怎样?菜园里今年都种了些什么菜?你父亲爱玩牌的毛病是不是收敛了些?外婆最关心的是麦子的妈妈,关于妈的细枝末节,外婆都跟麦子说得仔细而详尽。妈妈是外婆最小的孩子 ,三个孩子中唯一的女儿,外婆和妈妈的感情很深,在村里被传为佳话。
麦子最期冀的时刻终于到来了:外婆开始上演“精彩的华章”:开始讲故事了。外婆每次讲的故事绝不一样,连枝叶细节也不会重复。这些故事,都是从泥土里长出来的,无比生动,无比新奇,无比鲜活,极具生命力。为这一晚上的讲述,外婆几个月前就开始准备了。或是祖先在她儿时给她讲过的留在她记忆深处的,或是在村里和邻村听来的,或是她在生活里看到的和亲身经历的,经过她精心的组合、提炼、加工,再由她口里讲出来,新鲜得可触、可摸、可观、可感。外婆的体温混着被褥上浓浓的汗味,楼上堆放的粮食、洋芋味,屋后牛厩里的草料味,糅在了一起,黏在了外婆讲述中经过挑选斟酌的字句里和把握得体、句句入耳的语速里。这时,一字不识的外婆,俨然就是一位“故事大王”。这时,在这深山僻壤里,在这间庸常的农家房屋里,在这张松木大床上,在这稍显破败的棉被里,在这夜阑人静之时,相差半个多世纪的一老一少,相拥而卧,相拥而喜。人性的光辉,从古驿道上的马蹄声里,从祖先的布衣敝屣里,款款而至,涌动而来,照亮了这间小屋,照亮了这一老一少的心灵。
麦子感到外婆是在用她那一年四季在地里劳作、长满茧子、甚而是伤痕累累的大手,混着她的心愿和希翼,在麦子的内心种植一棵棵爱的幼苗。她坚信,这些幼苗会沐浴着阳光雨露茁壮成长,像坡地上的那一大片金桂,一棵棵神姿飒爽,香飘万里。
麦子走过一家豪华的奢侈品店。
偶尔,麦子也会走进奢侈品店,她仅仅只是为了长长见识和满足好奇心。她在那些贵得令人咋舌的奢侈品柜台前驻足良久,对那些设计精美、手艺高超的作品很是着迷。但她更加关注那些在柜台前优雅漫步、神姿仙态、气宇不凡的女人。她们被霓虹香风、高档化妆品和全身名牌打扮得精致优雅,颇像是柜台里的“奢侈品”。不少的或局部或整体做过整容手术,弄成了连自己都已分辨不出的另一个自己。她们像机械生产的同一产品,失去了自然天成、宝贵的独一,辜负了上苍的造化,让人扼腕叹息。难怪,很早就流行整容的韩国,现在都主张尊重造化,反对盲目从众。这自然是自我意识的觉醒啊!
麦子来到一条八车道宽阔的路口,加入了被红灯拦下的等待过马路的庞大人群。人群中不乏从农村来打拼的人,有快递员、外卖小哥、送桶装水的、送煤气罐的,麦子很容易就把他们从人群中区分出来。他们大都身着短衫,骑着摩托车或电动车,身体健壮,红光满面,汗流浃背,浑身充满活力。他们全神贯注,两眼盯着路对面的红绿灯。只要绿灯一亮,他们便率先敏捷地飞身而去,过了马路,一晃便无影无踪了。当然,也有在马路上很少露面的月嫂、保姆等。当然,数量更为庞大的是工地上的农民工。他们用辛劳的汗水和智慧,改变着城市的面貌,其中有不少人办了城市户口,融入了城市。中国每年有一千万人涌入城市,影响和改变着城市的“脾性和气韵”,他们以自己的身体力行,无形地“敦促着、推搡着”一些人止于荣华、沉迷享受的脚步。
石松就是这一群人中的一员,是这些“打工者”中的佼佼者。他高中毕业十八岁时进城谋生,做过送水工、送煤气罐工,当过建筑工。他在一家饭店里打杂时,因工作卖力,被老板送去学了两年厨艺,回来又当了三年的厨师。这期间,他结识了一位在政府部门管理经济工作的科长,科长见他十分聪明好学,又能吃苦,又有创新头脑,就给他出了个“金点子”。石松按科长的指点,花费了十多年的时间,边贷款、边建设、边经营、边融资,最终做成了一个集种植、度假、餐饮、避暑、演艺为一体的大型旅游文化项目,能满足各种人群的种种需求,成为了民营企业中一个非常成功的案例。
麦子上大学后,会常常梦到外婆给她讲故事的情景。在梦中,她会为外婆讲的故事添枝加叶,使之更加生动丰富。这让她很自豪,她成了外婆讲的故事的真正拥有者。外婆虽然离开了人世,但她却永远活在麦子心里。
外婆去世的那天早晨,麦子接到父亲的电话,说外婆病了,病得很重,外婆想最后看麦子一眼,这是外婆唯一的临终愿望。通完电话后,麦子哭了。麦子是从大学的课堂里走出来的,她站在教室外面接的电话。她抑制着,没有让自己放声大哭。麦子摸摸自己身上的银行卡,认定银行卡静静地躺在内衣口袋里,卡里刚好还有回家的路费。她没有向任何人说起这事,也没有向学校请假。这些,在她看来已是无足轻重的了。她赶到银行,取了钱就直奔车站,把中午的饭钱都省下了。
麦子跨进外婆的家时,已是晚上十点。她来到外婆床前,床前围着一大家子亲人。见她来了,都含着泪水迎着她。妈妈拉着她的手,哽咽着说:“孩子,你终于来了。外婆一直在叫着你的乳名啊!”
麦子俯下身来,趴在躺在床上的外婆身上,流着泪说:“外婆,我是麦子呀,我来了,你睁开眼睛看看我呀!”弥留之际的外婆听到了麦子的声音,睁开了眼,眼里荡漾出慈祥的光亮。她用尽全身力气,握住了麦子向她伸过来的手,断断续续地说:“麦子……麦子……”声音渐渐小下去。麦子感到,凝结在外婆手上最后的力气,在一点点弱化,生命的最后一片落叶,终于飘然而下,飘向缥缈的时空,归于茫茫的大地。
外婆的脸上,定格成了一个永远的微笑,那是她对自己的生命作出的“一个知足者常乐”的评价。
麦子的眼睛湿润了。
麦子看着擦肩而过的人流不觉想到,到底是因为什么一定要从农村挣脱出来,来到这个陌生的、人声鼎沸、举目无亲的城市。是因为农村贫穷、落后、守旧,而这里却繁荣、富有、浮华、先进、给人提供了可发展自己的更多机会吗?这些都是,但又不完全是。麦子感到,这其中还有更为深层的理由,那又是什么呢?麦子说不清,道不明。麦子奇怪,当她尚未理清这一切时,便有些身不由己地被一股巨大的力量推拥着、裹挟着进了这个庞大的人群,这大概就是潮流吧?
麦子最终上了地铁。
高峰时段已过去,车上已不拥挤。一位姑娘挪了挪身子,空出一个位子,用眼睛示意麦子坐到她身旁。麦子用一个甜甜的微笑,回报了姑娘的好意,坐了下去。
麦子留意着一个个或站或坐的人,他们都穿着得体,神情散淡,脸上自然地流露着他们是这座城市的一部分的自信和是这儿的主人等满满的自豪。
广播里不停地播报着车子到达的终点站和行进中的站名,语速从容、亲切,充满着无以言说的“诱惑”。
麦子到石松的住处,只有五个站了。随着一站站次第减少,麦子心中的爱情和温馨也在次第生长。不多时,她就进入到了一种意念的情境中,渐渐淡忘了所处的环境,从车上的人群中疏离了出来。她想到了即将来到的时刻,石松会以什么样的身姿迎接她?又会以怎样迷人的话语打动她?麦子知道,近一米八个子、表面高大威猛的石松,却深藏着一颗细腻的心。麦子要揣摩出即将在眼前展现的石松的种种细节,来证实自己预见的准确度,为她的推断打出一个高分。这不是儿戏,而是她对石松认知的一个检验。
这时,她无意间看到车上有两个男孩在注视她,她的脸一下子红了,像是心中的秘密已被泄露了一般。
麦子下了车,来到石松门前,拿出钥匙,开门进了屋。
麦子径直走到桌前,她从身上拿出家乡茶厂生产的金桂花茶,沏上一杯,摆放到桌上。即刻,金桂飘香,盈满屋内。
又是一个人流车流的高峰,虽然离早晨上班的高峰时间已过去了四个小时,但每条路都塞满了车和人,每个人都在按自己被规定了的路线行走。人人都明确自己要去什么地方,却无法知晓那地方会给他们带来什么。没有人知道下一个小时会发生什么,世界和人生都充满了不确定性。汽车也是。车流长蛇般缓缓移动,或者被红灯拦下,在有序中或浮躁中井然爬行,在烈日的炙烤中喘着粗气。而在这个别墅区,在这间别墅里,麦子和石松的“戏剧”还将继续上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