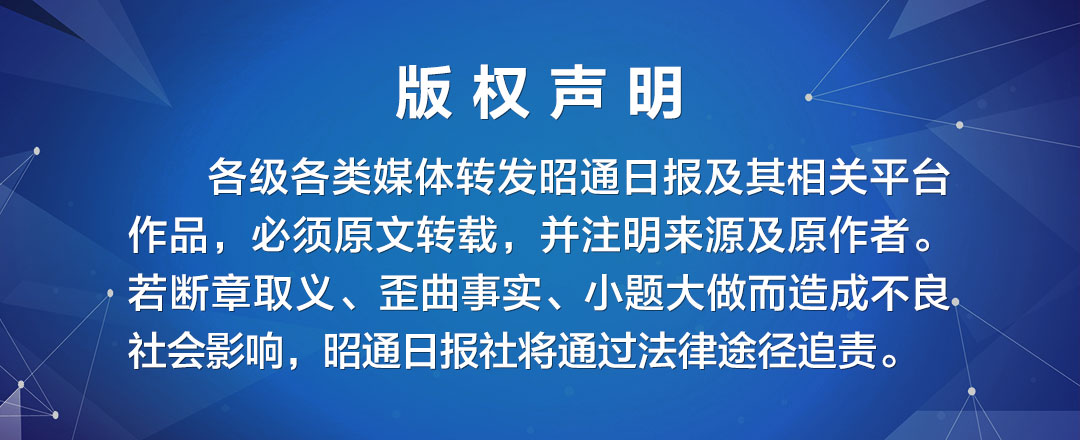2021-03-17 11:53 来源:昭通新闻网

房子的故事
◆陈正勇
2000年,我们一家租了一套房子在昭通城东后街,正处于爬坡地带。当时的东后街还有很多瓦房,那里的住户大多是农民,都还种着地,他们的地就在现今的省耕国学文化公园一带。东后街迎街的门面大多是商铺,有卖衣服的、卖百货的、理发的、摆地摊卖古董古币的……有一家夫妻俩,就着一面土墙,炉火通红地铸造各种型号不一的铝盆。土墙颓败,土墙后面的一棵女贞树,却长得青枝绿叶的。
东后街稍背的门面,迎街稍高的楼层,也随行就市地开了大大小小的歌厅,歌厅的名称五花八门。夜幕降临,城市更加喧嚣,装饰着各种色彩的霓虹灯,幻化着繁复的光。
我们租的房子,被两边的楼房夹在中间,终年背着阳光,阴暗潮湿。房间的设计也是住家的格局,门楣展不开,招揽不了生意,注定只能住人。
失眠的夜,对面街的歌厅,附近的或稍远的歌厅,传来各种嗓门的歌声,比着赛似的,粗的、细的,声嘶力竭的、憋得要断气的……直往耳朵里强行灌入,裹挟着人的神经,让你失去控制地跟着亢奋,跟着忧伤,跟着颓废。
躺在床上,强迫自己闭上眼,越想着睡,大脑越跟打了鸡血一样兴奋,打鼓的、摇铃的、敲玻璃杯的,声声敲在心坎上。歌声一拨一拨地响在枕头边,歌听了一首接一首,重复了一遍又一遍。终于,稠密的混响就像星子一样寥落了、消失了,午夜的街也忽然深邃而寂静。窗外,有夜行人走过,谈话声近了、远了;夜猫在瓦房上打斗一阵也喵呜着去了,只剩夜风掀动着烂塑料袋发出寂寥的沙啦声。当万物正要安恬地睡去,谁知道白天里不敢进城的大车又来了。先是一种闷雷似的声音,轰隆隆,接着车开始爬坡了,笨牛一样喘着粗气,响声越来越近,越来越大,轰轰轰、哐当、哐当……车身被坑坑洼洼的地面颠簸得跳起来,床便跟着一阵地震般地战栗。如果来的是手扶式拖拉机,那破铜烂铁般的嘭嘭嘭、嘭嘭嘭……吼得让人想吐,你能感觉到车头扭来扭去,车身打着摆子似地抖动着,散架似地挣扎着上坡,腾起一团又一团令人窒息的黑烟。
三室一厅的房子,每年租金一千八,彼时我们的月工资还不足一千。租金不菲,房东却把光线最暗的最大的一间锁着当仓库用,里面堆了破家烂什,还有许多洋芋、包谷。
房东的儿媳,那个肤色微黑、绑了大辫子、眉心里有一颗美人痣的年轻女人,有些像印度美女,常常用尼龙袋来拖包谷、洋芋,大概考虑到打扰我们的频率不要太高吧,每次来,总是把袋子装得又满又沉。太沉了,自然拎不动,拎不动,小女人就拖着走,扭着腰身,黑辫子在细腰上悠来悠去,尼龙袋拖得哗啦哗啦响。
这悄声哑气的小女人喂着猪,一到黄昏,猪就哼唧哼唧地叫,鸭也跟着叫,嘎嘎嘎地,最容易让人想到缺吃少穿的年代,心莫名地慌。
幽暗的房间,偶尔会从窗户里飞进一只只小鸟,有时是偷吃的麻雀,有时大概是人家养熟的画眉什么的,胆子要大一点,站在木格的窗棂上,一声声地叫,歪着头听回音;如果麻雀飞进来,一见人就吓傻了,愣头愣脑地乱扑乱飞,通常是只往亮处扑,把窗玻璃撞得咚咚响。
有一次竟飞进一只蝙蝠来,绕着天花板团团转,好奇又胆小的女儿吓得尖声叫。蝙蝠这东西来自湿冷昏暗的环境,飞得让人心里发毛,生怕它带了什么病菌,急忙打开窗子,可是蝙蝠偏不走,打开门也不走,还是飞,飞,不知在迷恋什么。
出租屋实在难住,吵闹,黑暗,精打细算的房主人,控制着水量,麻线粗的一股水,要死不活地流,还有时间段限制着,平时只在早晚供水,周末全天供水,供洗浆用。卫生间的水像游丝一样细,倒是长年不断,流在大塑料桶里,用来冲厕所。听说,麻线水,水表不会动。水流量太小,做饭还好,洗衣半天洗不完。衣服洗多了,房主人又不高兴了,就成天黑风丧脸的,女儿稍跑动得大声一点,女主人就在楼下粗声大气地警告。后来我们就给女儿买了两只红色的螃蟹,让她放了学安静地养螃蟹,做作业。周末就到二姐家玩,让她跟着两个老表玩。二姐家的房子虽然破,毕竟是自己的家。
2000年,我们到了城里,却是城里的漂泊人。
有一次在二姐家说到出租屋,忍不住红了眼睛。正在抽烟的二姐夫却说,得了得了,宽房大屋的住着,风吹不着雨淋不着,要去哪里,还有人瞧着。他们就在这黑旮旯里,一住还不是几十年。当再说到房租时,二姐夫才牙疼似的闭了嘴,阴着抽了半天的叶子烟,末了说,是了,是要打算着买自家的房子了。
2005年,我们节衣缩食,终于买了套二手房,终于有了自己家的房子。
二姐家却依然住在二甲,二甲的老屋是木质结构的,四角竖了四根木柱子支着倾斜的房梁。老屋百年沧桑,被两边的房子挤得收缩成一团,并努力像右倾斜着寻找依靠,一副摇摇欲坠的样子。二姐夫说,没事的,穿尖斗榫的房子最抗震,没事。
老屋的右边,赵家的楼房后来翻修时抬高了地势,这样一来,二姐的房子,地势更加落窝。房顶上成年累月地长着石莲花,肉嘟嘟的,苍绿的叶片,长老了就开一种穗状花絮。如果对石莲花感兴趣了,只要站在门前的门槛石上,用不着踮脚,一伸手就可以从房子的瓦楞上揭下石莲花。
到了晚上,老屋的石墙根脚,木柱子下的石缝里,传来蟋蟀的叽叽声。
老屋坐落的地势低,每次天降大雨,就到处进水,人忙得晕头转向,要不停地忙着把淌到屋子里,聚到灰洞里的水,一桶桶舀了倒出去。灰洞深及膝盖,一到雨季,即便不下雨也聚了水。
有一次奇怪得很,天空蓝天白云,太阳朗照,天没降雨,老屋却激流涌荡。我去的时候,吓得睁大眼睛,盆漂起来,鞋漂起来,二姐用来舀水的瓢也漂起来,门槛下一股水兀自汩汩地冒,像一朵盛放的莲花。莫非二姐住在龙脉上,龙王要出行了?我忙不迭地跟着二姐舀水,心里狂跳着,边舀水,边惊呼:背时了,背时了……在一旁忙得皮塌嘴歪的二姐夫听到,气急败坏地纠正,哎,五孃,要说,运气来了,运气来了!我心中一惊,忙不迭地点头,嘴里默念着:运气来了,运气来了。可是舀着舀着,水不见退,心一惶急,又忘了,又开始喊:背时了,背时了……
后来,水厂的人来了,到处查原因,原来是地下管道破了,水往低处走,就完全倾进二姐的老屋里。
遇到地震,我更是心神不宁,还不等地震波跑过,就忙不迭地打二姐的手机,通常是盲音,打不通。打不通就接着打,打得天昏地暗,仿佛听到木柱子断裂的咔嚓咔嚓声,椽皮墙瓦倾塌的哗哗声,越打越慌,直到打得听见二姐的声音。听到二姐的声音,就知道老屋安然无恙,二姐没事。
2010年,我们再次搬了家,我们终于有了一套房子,住进了环境更好的小区。小区隔着昭通大道就是实验小学、碧桂园小区、省耕山水小区。二姐住的房子在城中村改造中,一套还了两套,二姐住进了回迁房。
二姐原来住的老房子,后面原是一大片瓦房,据说是被遗弃的豆腐厂。记得每次从那里过,钻进曲里拐弯、黑咕隆咚的小巷,去到西街,就看到沿路颓废的瓦,歪斜的梁柱,倾倒的椽子。晚霞残照着,墙头上,狗尾巴草摇着夕阳的光。而今这些早已无迹可寻,二甲在今天,也可能只是记忆中的一个地名,人们更关注在意它的现世——洋人街,洋人街上的皮草与繁华。
最近些年,二姐和儿子去了大上海,在上海繁华的城市里,二姐的儿子,买了自己的房,有了自己的家,不再是繁华世界的漂泊人。只是二姐夫,一生的念想,最远的远方,只想到昆明动物园看老虎,终是没等到。
走在日新月异的城市里,穿行在一个比一个漂亮的小区间,徜徉在依山傍水的乡村别墅群落里,看日落日升,樱花迷醉,苹果花开如潮,常让人恍兮惚兮,似梦似真。
(作者系昭阳区第二中学教师)
 (陈正勇/文 图片来自网络)
(陈正勇/文 图片来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