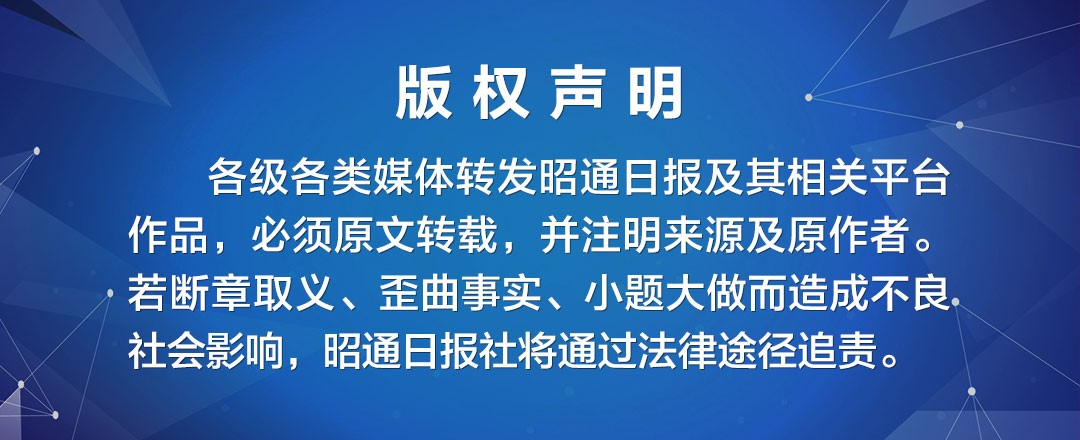2021-03-02 17:39 来源:昭通新闻网

我不是特别想写有关故乡的文字,总觉得这个主题已经被别人写得很“烂”和“俗”了,但随着年岁的增长,越来越觉得对于自己的故乡,尚有许多未尽之言,这块从出生起我就“缺席”的土地,随着时光的流转,一点一点地回来,我身体里流淌的血液因子也开始一滴一滴地注入了某种悲伤。这种悲伤越来越浓稠,我想,如果我一直保持缄默,它会不会在我体内凝结成固体,让我永远化成一块在他乡的“望乡石”呢?
我必须得为它写点什么,留下点什么。
一
不得不坦承,时光就像水银柱一般缓慢侵吞着我的记忆,故乡的面貌也在这种啃噬里逐渐变得残缺不全。如果硬要回忆,那勉强可说的,就是四五岁时第一次在父母的带领下,和哥哥一起回老家时,看到的那条在田间里涓涓流淌的小河以及高中毕业第二次同父亲回老家时,出现在衣服里面把我吓得半死的“虱子”。
我并不想感伤那些如今已不复存在的溪流和泥鳅、小蟹,田地和村庄。不管你情愿不情愿,大地与人的连接正在以各种方式异化——历史发展下的城乡面目在每个时代都有所不同,我并无可能评判这块大地在现在和几十年前,几百年前,甚而千万年前,哪种面貌更好一些?
所以,我并不想感伤。唯有失落,因为我这一生的时光曾有那么一丁点儿是留在这里的,而我的生命,还是得回来。父亲、爷爷,对一个家族的两代人来说,这块土地早已烙下了“足够的印记”。
当我的身体和这块土地渐行渐远的时候,内心有一股缓慢滋生的力量,隐秘地、不可阻拦地和皮囊逆向而行。
二
很多年以前,在我还是个小女生的时候,乘坐着一架对我来说简直就是庞然大物的“波音737”飞机,从边陲之地起飞,越过云贵高原,穿越重重迷雾,到了比天空更加苍茫的北京。17岁参军的叔叔在那里已经安家落户了,婶婶是某学校的英语老师,爷爷也在我去的前一个月被接到了北京。
飞机在下降,而我,贴在飞机的舷窗边,贪婪地往下看:巨大的城市像一幅辽阔的画,中间的空气却像一层深灰色的浓稠的纱,使来自地面的灯光闪闪烁烁,仿佛天地倒置,星辰在下。
到了北京,除了好奇,就是难受。每一个人,离乡的人,我想,最先作祟的就是“胃”。我们的胃比我们更有“乡愁”,更眷恋某一种食物。比如洋芋,比如酸菜,比如大米饭,比如所有不加小粉煮出来的任何一种汤。某日,我在厨房准备泡面吃,见爷爷紧皱着眉头踱着步走进来,手里捏着一个馒头,嘴里喃喃地说:“跟吃猪食一样!”我忍不住笑了。原来爷爷也不习惯哦。
我已经记不清当时叔叔所在院子的具体位置了,但应该是很偏僻的,因为在北京那样繁华的京城里,居然还有一大片的地上,种着一些蔬菜。我因为总是弄不清楚蔬菜的品种而被叔叔笑话。
长安街、天安门、长城、故宫,我像一个陌生的误入此地的游荡者,唯一的存在感是看见了镜子里的自己,那个以为自己已经长大了的小女孩儿。
我离开北京后不久,爷爷也回到了老家。那个曾经可以肩挑一百公斤的矍铄老人回到昭通后便一病不起,北京那一次竟成了最后的见面。直到如今,我脑海里的爷爷仍然是那个穿一袭深蓝色土布长袍、裹着一个大大的黑色包头、脸膛瘦削、布满老人斑,似笑非笑看着叔叔院子里的那方菜地,仿佛在“嘲笑它太袖珍”的爷爷。
离开故土的人,为何会变得如此虚弱呢?
那是我第二次远离故土。
三
就跟东北人喜欢称呼女孩子为“丫头”一样,“姑娘”这称呼是我昭通老家人喜欢用的。自小被父亲和几个叔叔叫着“姑娘”长大,一直到现在仍然这样叫,每次说话前都会清清楚楚地唤一声“姑娘”。我呢,一听到这声称呼,心里头就先“柔软了三分,听话了三分”。
某日,一位昭通籍的老师发“微信”给我的时候,居然以“乔姑娘”相称,我这心,立刻就“化”了,立刻就“贴”了过去,仿佛对方成了我的亲人。
掰着指头算,约有20年未回过老家了——当然,如果上一次到昭通开笔会不算的话(因为那次除了开会和住宿,哪儿也没去)。
老李一直说我是“冒牌的”昭通人,我特别不服气:“凭啥我就不是昭通人呢?就因为我没出生在昭通吗?那也是因为我爹大学毕业后就到瑞丽去,娶了我妈嘛。我在昭通的亲戚还有很多呢!”
不过,老李这样说我也是有缘由的。娘是傣族,爹是汉族,因为出生地的瑞丽是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于是户口本上就随娘填了傣族。后来也是因为民族身份,幸运地成了鲁迅文学院少数民族高级研修班中的一员,所以大多人都只知道我是傣族,不知我的父亲是昭通人,是汉族。当时老李斜着眼睛说我:“你又想混进昭通噶?”这一个“又”字把我打击得气虚不敢辩驳,实在是有理说不清,先是“混”进了少数民族作家群,现在“又”想混进昭通作家群——谁都知道昭通的文学群在中国赫赫有名,作家们将国内所有大奖小奖都已收入囊中。所以我这心还是很虚的:我为何竟没有遗传到这等天分?
2019年5月,我参加云南省报告文学协会的年会,地点就在老家昭通。
19日飞到昆明,次日清晨,丽海和老李到酒店接了我,我们都坐一辆车从昆明出发。车上,老李开玩笑说我这是“荣归故里”。我一下子脸热心跳,羞愧起来。明知这不过是一句玩笑话,却在心里跟自己“较真”了起来。
古人要富贵了才归故乡,而我半生一事无成,财不足置办豪车大宅,权仅够支使家里一只小狗,何谓“荣归”?
父亲是家中的老大,毕业后原本是应该分在昆明军区做一名军人的,却阴差阳错,“命运拐了个弯”,被分配到了瑞丽。也就在这里,他和母亲相遇了,完成了命定的一场姻缘。和所有相爱而结合的男女一样,对爱情和婚姻抱有天然的乐观主义进入,后来却不得不狼狈不堪地挣扎着游出这方“泥塘”。
若是以世俗标准来看,当时的父亲在事业和婚姻上算是略有成就的:年纪轻轻便已进入管理层,一儿一女。随着父亲根基日渐稳定,老家的几位叔伯兄弟也来到了瑞丽,各自也都有了自己的落脚点。这样看,父亲这一代的家族似乎进入到了一个“鼎盛的时期”。
20世纪90年代的瑞丽,正是改革开放后最为繁茂的时期。如同泄洪的闸,人群和财富从各个通道四面八方蜂拥而至,翡翠黄金、红蓝宝石、水晶玛瑙……让人目瞪口呆、应接不暇,伴随而来的自然还有不可测的风险和跌落。昨天还是挑着担子卖卤鸡蛋的小贩一夜之间就成了大饭店的老板,今天还是“钱包充实”的商贾,明天就成了不名一文的穷人。
如果没有那一年的意外,我很有可能成为一位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大小姐,可是命运之手从来不容人抵抗,它将我家撕成了碎片。人类的贪欲已是原罪,自出生便随附而来,终生与之作战。父亲没有足够的力量与意外对抗,有了很多而又想要更多,一次足够高度的“跌落”让他终身无法“从容地翻身”。从那次意外发生以后,父亲性格大变,怨气满腹。我也开始畏惧每一次跟他的接触,因为每一次见面唯一的内容就是听他骂所有的人,骂“该死的婚姻”,骂这个社会,从30年前就开始历数“罪状”。我悲哀地看着腰背尚且挺直,发须尚还黑密的父亲,终于有一天,我打断了父亲的话:“爸爸,如果你一直活在过去,那你永远就没有现在和未来。”“未来?我都这把年纪了,早死早好!现在过成什么样子了,不要你们管!”父亲依旧中气十足。“可是,爸爸,我从小看书,看到的都是年长的人可为年幼的人作表率,长者都能看淡所有的争斗,可是在我们家,为什么不是这样呢?我一直看到的都是你们之间的争斗和不原谅,这是你们要教给我们的吗?”
听到这句话后,父亲不再发怒,突然就沉默了,低头只呼噜呼噜地吸着他的水烟筒。
从那以后,再没有听他抱怨过什么。整个人,突然就平和多了。
受父亲那次事业下跌的影响,几位叔叔的境遇也开始走“下坡路”。在城市生活过的他们,又如何回得去?欲归家无人,欲渡河无船。如今,一个个如离枝的叶子散落各地,正为一家老小拼尽全力地 “和生活死磕”。
四
按照我现在的回忆,爷爷的家应该是在农村,而且有阁楼,屋子中间有个火塘,地面是由深褐色的又带点红色的胶泥土压成,被奶奶清扫得一尘不染。屋外是一垄一垄平平整整的田地,当时种的是红萝卜。记得这么清楚,是因为我去偷吃过。红萝卜翠绿的叶片既小又柔弱,细长,有一些软软的绒毛,我将它的叶子拢在一起,向上轻轻一拔,一根和我手腕差不多粗细的红萝卜便被我拔出来了。红萝卜纤长的身体带着湿漉漉的泥土,有一种透明的晶莹质感。我至今清楚地记得它入口的滋味,还带着初冬时霜的冰冷,被霜冻过的红萝卜,仿佛有着一种举世无双的清甜,所以,这滋味,我至今不能忘记。
比之红萝卜,昭通的洋芋,我吃了那么多,印象却有点模糊了。
洋芋是第二次回老家吃的。父亲开车带我去的。
洋芋和昭通酱,它俩是绝配,这是我那次的发现。
奶奶把洋芋放在屋子中间的火炉上烤,还没烤熟,一股焦香味就像钩子般地钻到鼻腔里,把我的“馋虫”给勾出来了。没烤熟之前奶奶是不给我们碰的,直到外皮烤成了黑黑的一片,用瓦片刮成脆脆的焦黄色,她用一根筷子去试探:如果筷子能很轻松地插进洋芋的身体里去,说明熟了,反之则还不可以入口。熟了以后的洋芋,奶奶用两个手指头飞快地将它提拎起来,另一只手则迅速用靛蓝色的粗布衣襟接住,掸掸灰,拍打拍打,便放在一张小小的草纸上,蘸料是她早已放在土碗里的昭通酱。如果洋芋烤熟了的时候奶奶刚好不在,我们就会争抢,一个个都快成年的大孩子,还像小顽童一样地抢来抢去,洋芋就一个个地满地打滚。
一次和哥哥吵了架,我赌气不搭理他好几个小时,他就一直在我面前绕来绕去讨好我。我跑到火塘边坐着,扔了个洋芋进去,快熟的时候他又跑来了,站在我面前嘻嘻地笑。我没好气地说了一句:“快让开,别对我的洋芋虎视眈眈!”话一出口,自己就忍不住“扑哧”笑了起来,妈呀,“虎视眈眈”我的洋芋!哥哥听后,笑得要打滚,屋里所有的人都乐不可支。正笑着,突然闻到一阵很“臭”的味道,赶忙四处寻找,却发现是自己的脚踩在火塘边的铁条上,橡胶鞋底被烙出了一条印痕。
再一次,爷爷坐在火塘前一个人呼噜呼噜地吸水烟。他披着件灰蓝色的布衣外套,缠着深蓝色的布包头,一双手纳的黑色粗布鞋,灰白色的胡子大概有我半只手掌那么长。我拿了几个洋芋放到火塘边,用灰埋起来,坐在旁边的爷爷笑起来:“小丽,你那么爱吃洋芋呢。”我“嗯”一声就准备走,爷爷把我叫住,说要跟我摆摆“龙门阵”,于是我只有乖乖地坐下来了。
爷爷一边“呼噜呼噜”地吸着水烟筒,一边跟我讲:“你们在宣威、会泽和东川还有三个奶奶哩!”我刚把嘴巴张大还没来得及其他反应,就听见奶奶的声音从门口传进来:“那你是不是还要带着他们去认识认识呢?”爷爷吓一跳,赶紧换了个话题,仿佛刚才说那些话的人不是他。蓝布长衫黑裤子的奶奶白了他一眼,踮着小脚又出去了,我则乐个半死。这件事后来被我当成家里的趣事说了好多年,但一直到现在,爷爷奶奶都故去了多年,我也不知道那三个地方是不是真的还有我们的血脉亲戚。
后来爱吃洋芋到什么程度呢?天天吃,顿顿吃;在家吃,出门还要花钱买了吃。街上的吃法并不多,大概就是三种,烤熟的居多,可能是因为方便,推个三轮车就可以四处叫卖;另外还有两种,一种是类似于我们现在吃的麻辣烫,洋芋切成一片一片的,用竹签穿起来,烫熟了后抹上各种酱料吃;一种是油炸洋芋,蘸料又分两种,干辣椒面或者是昭通酱。出了门,见到哪种就吃哪种,完全不挑,因为一样地好吃。至于在老家里做了吃,那吃法就多了,除了烧的烤的油炸的,还有炒的、煮的,整个地蒸的或切丝煎饼的……至于吃相,那就草莽得很了,怕烫手,就将洋芋整个地插在筷子上吃、一面换手一面用嘴呼哧呼哧地吹着吃,比较经典的是蹲在地上双手“颠”着吃。各式各样,各形各状,回想起来真是好笑得很。在老家的那半月里,我胖了近10市斤。同时带来的后果就是在往后的20年里,我再也不敢“碰”洋芋了。
后来听说,在1948年,边纵部队1200人赴越南河阳整训时,400人死于恶性疟疾,其中绝大多数是滇东北人,他们临终前唯一的愿望就是能吃上一个家乡的烧洋芋。
苹果和往事有关。
那年的我爱上了一位男生,准确的表述应该是:我和一位男生相爱了。他“宠我是宠到没边际,宠到没有底线”的那种。现在想来真是唏嘘,那种狂野到不过是寻常暂别却如生离死别一般的断肠和痛苦,那种在大庭广众也忍不住仿佛要把对方揉进自己身体里去的死命拥抱和痛哭,那种可以为对方舍生忘死的“痛快”,如今再也不会有了,今生也不会再有了。只有那时的我们,才拥有对时间的放肆,拥有对自己生命的主宰权。现在却唯有一声冷笑,我们的命哪里还是我们的?不要说死,连生病都害怕得要死。是啊,“死了”,谁来照顾我们?谁来照顾需要我们照顾的亲人?
他和我是异地恋,但因我一直自诩为流浪儿,并未在意空间的距离。
苹果就是那个时候吃怕的。他见我爱吃,便一箱一箱地买了来给我,哪怕我回到老家,他也寄了来。那个时候,在整个云南省,都是昭通苹果的天下——即便是交通网络如此发达的今天,昭通苹果仍然占据着半壁江山呢!
空间的距离可以忽略,两个人的性格却无法忽略。
年轻与气盛,总是相依相生。针尖对麦芒,也总是形影不离。时间久了,吵闹得倦了,便拼了死地分了。爱到尽头覆水难收,不如一别两宽。
时光漫卷,那份情感也早已时过境迁。但即便到如今,每每看见昭通苹果,仍是忍不住地想起那个人,想起那些整箱整箱的苹果。
五
父亲17岁离家,如今已白发苍苍,已近80岁。
我,从出生就缺席的人,在黑夜中,回到这块养育了父辈祖辈的土地上,一路地寻找到昭通。父亲的长安车“奔奔”在这样的道路上显得笨拙但实用。对于回乡的路,父亲显然也不太记得了,一路行一路问。刹车、询问、起步,给油。接近那个叫“28户”的村庄时,心里竟然惶惑起来。
父亲在逼仄弯多的村里土路上驾驶着车,显得手忙脚乱,还要记得时不时给我指出,这儿是家里的老宅,那里是我二叔现在的家。目瞪口呆地看着这一切,我曾经来过的这里,现在,它们三分之二的地方被垃圾、土基、沙土和一些面目不清的堆积物所覆盖和掩埋,三分之一突兀地盖着崭新的楼房。父亲看出我的情绪,他只是笑:“发展过程么,都是这样,再过几年就好了。”
是的,这是我的老家,一个真实的村庄,并不是文人心目中的田园。
新的覆盖了旧的。旧的被新的取代。淹没、填充、层叠式的覆盖,遗忘了遗忘的伊始。
这种覆盖,是碾压式的,极具毁灭性的,或者也可以以“再创”而代之。
零乱和规整,局部和整体,唏嘘和欣慰,交织成一张庞大的网。
我站在现实,却被过去淹没。
记忆中的故乡是冷的空气,甜的苹果,香的洋芋,时至今日,时间已经将这种种,全部发酵成一个血缘式的名词:昭通,昭通,昭通!
文字中离不开的故乡,对应的是现实中倾尽半生也难以回去的离人。
抵达熟悉,却如抵达陌生。
抵达陌生,却是抵达熟悉。
六
每一个人,都是被关在故乡里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