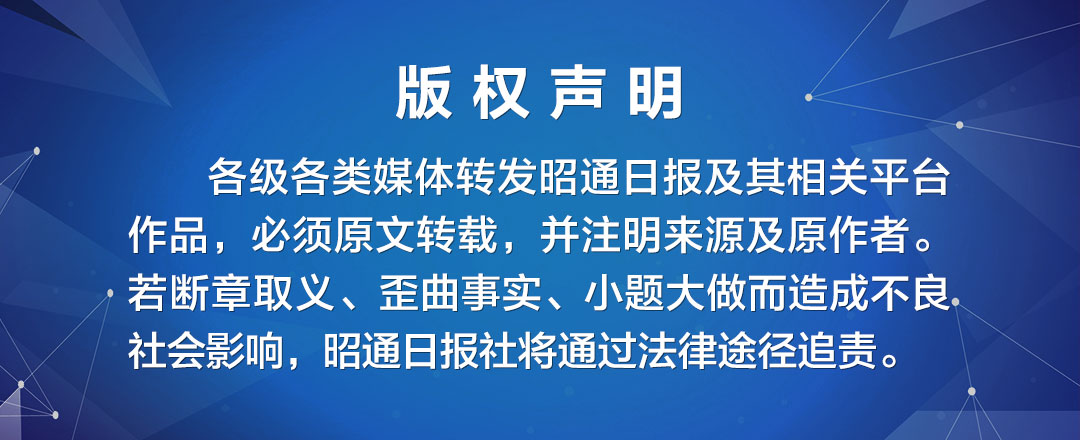2021-03-01 15:32 来源:昭通新闻网

尹 马 生于1977年,云南镇雄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有作品发表于《人民文学》《诗刊》《青年文学》等杂志,出版诗集《数羊》《我的女娲》等4部、长篇小说《回乡时代》、中篇小说集《蓝波旺》《天坑》、散文集《在镇雄》,曾获云南文学奖、滇池文学奖,鲁迅文学院第36届高研班学员。

王单单 1982年生于云南镇雄,曾获《人民文学》新人奖、《诗刊》青年诗人奖、华文青年诗人奖、云南省文学艺术奖等,参加过诗刊社第28届青春诗会,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2016—2017年首都师范大学驻校诗人,出版诗集《山冈诗稿》《春山空》、随笔集《借人间避雨》等,现供职于云南省作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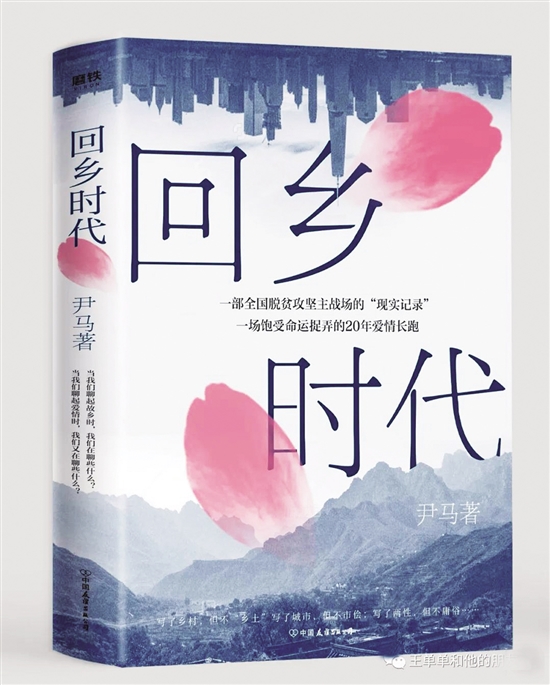
王:得知《回乡时代》已经出版,表示祝贺。作为一部文本字数多达40万字的长篇小说,在合上电脑的那一刻,你是否认为已经解决了“讲了一个故事”的问题?
尹:有没有“讲了一个故事”的问题容易解决,关键是有没有讲好这个故事。动笔之前,我考虑过以什么身份来讲故事,比如,说书人。后来我想,如果把情景设置在年关,茅檐内、火炉边,似有不妥。说书是要有腔调的,有腔调的表达更要求“章回”性,我讲的这个故事从年代上来说没有这个方面的结构约束,所以只能选择更为舒服的“井边谈话”。设想,两个挑水的人在井边相遇,随口说起近日见闻,索性撂下扁担神聊,东南西北,赵钱孙李,却都只是开场白,往往要聊很多很多废话才能进入正题,往往正题就是把扁担放上肩后准备说的“最后一句话”,比如:隔壁寨子里彭家二姑娘回来了,你听说了吗?——其实《回乡时代》所讲的就是这个故事:一个男人离开一个女人二十年,一个男人找了一个女人二十年。离开她,难道是为了寻找?这绝非感情线索,而是命运逻辑。我这样讲,是想告诉你,故事从这里开始,也将在这里结束。
王:这些年来,你始终关注底层民生的每一个“现场”。就我们生活的这个地方,每一天都会有很多人在现实的捆绑中“来去”,从宿命论的角度来诠释故乡的属性。我是这样理解的:你写下这一切,并不只是还原生活真相那么简单。用一部长篇小说来成就一个庞大的“异乡团”,你最想达成的文本夙愿是什么?
尹:真相来自于平常生活的吞吐,是一种没有固定面目的客观反映。真相没有对错,只不过当它成为一种“现象”时,在特定环境和时间容积中所释放出来的力量就有所不同。生活在“人群”中,我们会用放大的情绪去感知人群的流向。在一个以“县”为单元来衡量人间冷暖、梳理众生命运的生活现场,我们可以通过人群的流动去获得民生色彩的定义。在每一个暂时被腾空的村庄,荒草蔓延的速度常常高于土地本身的能量,你所看到的炊烟竟然无法代表活着的“生机”——那么多人去了哪里?他们是否从内心信仰儿时的山河?是否在情感上留下现实理想上的回归?这个庞大的异乡团使命何在?(或者说,他们有没有使命)多年以后,他们有没有在场的证据?当然最根本的落脚点是活着,活出声响。《回乡时代》首先代表的是一种声响——求偶式的撕裂,归来式的慰藉或断送。
王:以一场爱情切开人物命运的走向,对构建一部长篇小说的框架来说,无疑是残忍的。当一个爱情故事变成“爱情事故”,置身于异乡的两个人如何在二十年漫长的煎熬中捏合、打开,应该是这部作品首先要考虑的问题。读到两人相遇之时,其实所有的悬念都已经没有了,然而我还是感觉到无比沉重。我想知道的是,小说故事呈现的原本是苦难的命运,你却自始至终都在使用一种比较轻松、诙谐的叙述语体,你是怎样实现这种“举重若轻”的?
尹:在这部作品里,爱情肯定不是阅读设置中的噱头,而是故事本身的一部分。或许可以这样说,在我拟订写作计划的时候,这个故事就像封面一样给了我一个先入为主的线索上的“迷惑”。在二十年前的中国农村,普通人物的爱情是干净的,他们从不怀疑自身血液里埋藏着的勇敢、执拗,“一起活到死去”绝不仅仅是一句“海誓”。把他们从中锯断的,是粗粝的现实,说到底,就是贫穷。代表了千千万万贫穷农家子弟的周楚阳,他的爱情理想当然也是“般配”——可靠的事业、看得见的未来,然而这些他都没有,“一夜的甜蜜”最后肯定就变成了一种“用纯洁伤害纯洁”的错误。周楚阳的出走具有无比可靠的现实性依据,而女主人公彭玉素最后放弃了一份优厚的教师待遇选择离开,让原本干净的爱情多了几分“赴死”的纯粹。我几乎想告诉所有人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只不过故事本身充满了小说功能所需要的各种“嫁接”,让贫穷坐实了它无限荒诞的“罪名”。从文本意义上来说,爱情肯定是美好的,所有交集、斗争、矛盾最后的归途,是让他们重逢,因为救赎,因为乡愁,因为故乡赋予他们共同的使命,当然,主要是因为爱。写作如果可以申辩,我想说的是,《回乡时代》故事虽然沉重,但讲故事的过程是不必要沉重的。前些年,我经常在年关搭乘绿壳乡村客运车回家去,和许许多多返乡过年的故人在路边说话,谈及谁客死他乡,他们总有着一副成功避开厄运的幸运者的面孔,习惯于在“谈笑风生”的氛围里给我讲一个死去的发小在远方的种种糗事,好像他的死始终无法避开那些“不合时宜”的经历。我习惯在这样的铺设里聆听,也习惯用这样的方式讲故事。
王:人们从一个边远之地潮水一样涌向外面的世界,这一现象在获得“劳动力转移”这一特定称谓之前,有很多不确定性。在中国南方,“打工”这个词的色彩是饱含热泪的,在“易地扶贫搬迁”这个民生工程没有实施的时候,解决“一方水土养不好一方人”的办法更多的是劳动力自发“输出”,去异地他乡搬运“黄金”。《回乡时代》写的就是这一群人,他们中的大多数甚至是举家外迁,在“回不了故乡”的那些年,他们只能仰仗流水线上的机台完成一个家庭的“人均纯收入”,根本谈不上“创业”,更谈不上“蜕变”。当然,有一部分走出去的人,抓住了命运的“后台”,赢得了自己的山河,成为成功人士,他们的故事,更是一部“血泪史”。在这部作品中,你写了很多成功人士,你把一个个“回乡事件”写成了“回乡必然”,是否真正遵从了“回乡”的时代属性?
尹:打工是我们这一代人人生的“证据”。上中学时起,村里的发小们辍学后,都陆陆续续去了远方。最开始,人们说的是“走,进厂去”,后来才说是“在外面打工”。最开始,打工也就是把一个个生活现场安放在离家很远的地方,无序进驻带来的危机四伏曾经成为热点蔓延,“到远方去”的盲目行动发酵成新的矛盾。在中国长三角、珠三角地带,一度时期内“蛰伏”着数十万“同县”,光浙江永康一个县级市,在最多时就有20万之众。进厂,务工,很多人每天都在寻找在异乡活下来的机会,他们肉体上的挣扎碾压着心灵上的苟且,每天都有不同的事件发生,每一个事件都带来巨大的创痛。我们的故乡,曾经因为有这样一个庞大的迁徙群体而成为一个锈迹斑斑的“巢穴”,在“劳务经济”还没有成为“支柱”之前,有几人能够衣着光鲜地回来,用具有说服力的生产力填补现实的空虚?《回乡时代》里的人们,经历着现实的鞭打、磨砺,带着自己的故事在远方安身立命,在时间的侵蚀中用破釜沉舟的勇气为自己“消肿”,他们中很多人的原型是我后来认识的成功人士,他们在外面的打拼、坚守,足以迫使一个写作者在用尽世间所有“带病”词汇之后仍然感觉到茫然失措。不容置疑,在“一方水土养不好一方人”的前提下,曾经因为贫穷而走不出大山的人们,他们离开时除了怀揣着对这片土地的绝望,还有对自己深深的自责、痛恨;当他们逐渐在异乡的土地上立下足,内心慢慢有了“爱恨交织”的感觉……其实,每一个离开故乡的人,都会把自己想象成从故乡射出去的一枚箭矢,梦想着有朝一日能够荣归故里,前提是他们抓住了活着的契机,把自己武装得足够强大。小说里的成功人士,是在故乡面貌向好转变之后看到故乡“可塑性”的一群人,他们的乡愁驱使指向是“回得来”,让自己的出生地能够支撑起人生的风向。当世界上再也没有漫长的等待,所有距离在慢慢消解成为各种“速度”时,回乡不再是一个事件,而是一种满怀期待、有着温暖牵引力的必然。“这是一个美丽的回乡时代!”小说完成后,我希望所有“对号入座”的他们都获得这样的思想自觉,因为这句话本身并没有错。
王:《回乡时代》给我的一个最深刻的印象,是你对人物性格的刻画。我似乎在所有人物角色的身上看到了一个共同的东西,即对逆境的不屑,这种往上生长的力量,就像你在作品中所写的县委书记赵云芃送给周楚阳的那四个字——向阳开放。除了讲故事的方式是温柔、幽默的,作品中的人物大多也比较温柔和幽默,这是否是你创作这部作品的一个初衷?
尹:与其他作品不同,《回乡时代》是我写给广大普通老百姓读的一本书,说白了,就是给广大离开故乡到外面的世界打工的农民工讲故事。在这本书中,每一个远在异乡的南广人都那么坚强、勇敢,他们每一个人都在命运的锁喉中寻找着“唯一”的出路,现实容不得任何人妥协或投靠,所以他们在生存或毁灭之间选择了一个冲锋的姿态,用“笑谈”的方式来告慰绝境中的磨难,向着有阳光的地方奔跑。周楚阳通过在浙江、广东等地十几年的打拼,练就了不俗的“功夫”,对生活中出现的种种困难、矛盾当然无所畏惧,尽管受到别人的算计,体味着寻爱之路的苦涩,承受着来自工作、生活等方方面面的压力,他仍然笑对一切,以谐谑的方式来化解疼痛。在一个被贫穷占领了日常封面的地方,每一个人都有一种来自骨子里的“向死而生”的决然气质,“奔赴”的意义在于打开命运逆转通道的可能性,在这个过程中,对生活的乐观态度当然是成就一切的最有效的方式。在这部作品中,南广人大多有一副“段子手”的面孔,和我一样,我喜欢在粗放的线条下养育一种天然的表达情绪,用这样的方式来完成一部长篇小说的叙事,会使作品阅读障碍最小化,会让读者感到一身轻松。
王:用一坡板栗来迎接自己寻找了二十年的女人,是男主人公周楚阳开启回乡路径的方式。你在坐实这一“故事主旨”之前,有没有对回乡创业者的思想情绪进行过一个清理?比方说,他种一坡板栗的初衷是为了还原少年时代的相遇情景,还是认真地发展一项产业?当然,故事讲完后,人们都明白是怎么一回事。我想知道的是,这个回乡举动是如何通过文本表达而立起来的。
尹:周楚阳回乡种板栗,是因为一段机缘,即“南栗”公司的顾羽之前找过他。他看好这个项目的主要原因,一是因为南广的板栗的确是“云端之上的好板栗”,可以做成南广的高原特色农业样板,市场前景看好;二是南广需要一个真正具有标志性的生态屏障,在获取个人经济效益的同时赢得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他愿意充当“第一个吃山螃蟹的人”。前者是一个商人的视角,后者则是作为一个南广人应该体现的社会担当。当然,在周楚阳的心中,“板栗树下”始终是一个美好的回忆。从“寻找”的角度来讲,他的内心有着还原少年时代“相遇”的情感冲动;从讲故事的层面来说,这恰恰是一个伏笔。小说是需要起承转合的,“有故事”才是硬道理。周楚阳回乡近两年后,女主人公彭玉素终于“看在这一坡板栗的份上”回到南广,其实是这个时代“有情人终成眷属”的呼应,最终避免了“用贫困伤害贫困”,所有的“想象力”也终于在一代人的艰难突围中迎来破茧和涅槃。
王:胡也频在中篇小说《到莫斯科去》里写了这么一句话:“在他的脸上,从疲惫于旅途的脸上,隐隐地浮泛着最天真的表情。”作为“实现有意义的人生”的通道, 各个时代的“旅途”都是承担着一定使命的艺术形象。社会前进的步伐,在很多文学作品中,都通过旅途生活体现出来。《回乡时代》中的旅途,是一群人寻找生活支点的旅途, 很难用“疲惫”这样的词语去详述,不过,我们倒是可以从每一个人的脸上看到“最天真的表情”。一段旅途昭示的人间力量,是否可以作为一代人摆脱藩篱追求幸福的见证?
尹:小说里的旅途,实际上是对远方的抵达和对故乡的归来,是一段漫长的人生历程。《回乡时代》里的一群人,如果对照现实的话,很多人的旅途是立不住脚的,因为他们仅仅是为了活着,而没有通过获取尊严来体现“天真的表情”。但对于周楚阳、彭玉素、朱立东等人,旅途的意义在于他们通过“出”与“回”的过程来促成个人思想的进步,推动自身理想的实现,让“回乡”成为这个时代的使命和必然。委实说,在这部作品中,我写下的旅途是轻于远方的,因为小说人物行程上的来来回回并不足以支撑一个庞大的群体自身的起点和归宿,因为更多的事件是生发于“远方”这个地域概念而并非“途中”这个时间概念。然而,如果就小说人物整个生命历程的重量来衡定的话,却只有旅途最可靠,因为故乡与远方之间横亘着的距离,除了要在里程上实现到达,更需要在心灵上实现跨越。“远方本身没有太多含义,只有在特殊语境下,才会被赋予希望、希冀和愿景之意。”从这一点来说,只有旅途绕不过去。
王:从你的创作履历来看,你属于少年成名的诗人,从14岁开始,到现在你已经写了30年的诗歌,而写小说则是13年前的事。2011年,你的第一部小说集《蓝波旺》出版,后来又是《天坑》,前前后后,你应该发表过中短篇小说30部左右。大多数人只知道尹马是个诗人,我认为并不奇怪,因为你是写诗起家的。而在业内就不同了,很多人认为,你的小说有一种与众不同的民间色彩,无论是叙事方法还是语言,都有一种民间歌谣的“律动性”,是当下“民间经验”写作的另类典范。你能否结合《回乡时代》谈谈你的小说创作?
尹:作为一个诗人,我始终认为我一直生活在“乡下”,和其他深谙民间物事的底层写作者比起来,我也有不一样的地方。我在坚持小说乡土精神的基础上,追求用诗歌的节奏成就小说叙事的律动、隐忍和通透,努力让作品具有阅读上的“感官性”。其实,我的理想就是做一个钟情于讲故事的“段子手”,注重构筑小说情节的视觉现场感,让作品具有较强的戏剧冲突效果。《回乡时代》作为一部长篇小说,肯定不能在以上方面得到更多呈现,但有一点我是可以肯定的,即在借力“真相”呈现事实图景的同时,将写作现状化、溯流化,使它成为一种谈笑式写作,真正让乡下还原为乡下、让生活承认生活、让计谋回避计谋。我认为,我的这部作品应该具有“故乡流传化”“故事喜剧化”“诗歌陌生化”的特点,具有感叹式的声响和启幕式的色彩,应该能让人在阅读中找到一种“眼前的下落”。当然,在这部作品中,最显著的特点还是“时代类型”,即与当下时代特征切合、融入度高,更像是广大游子精神上的“更路簿”,这样的“有意”创作,是会成就作品超强的镜头感和现场感的,且有非常明确的影视改编方向,具备打造成一部主题明朗、内容贴切、画面温暖、感染力强的电视剧先决条件。
王:镇雄曾是全国脱贫攻坚的主战场,也是革命老区。我认为,生活在镇雄这样的地方,有的是民生大事的体验,有的是生命极处的感悟。在这样一个边远之地,你是否还会以一个作家的身份为这片土地写下更多的东西?
尹:镇雄出产土豆,也出产作家。我在这里生活,肯定避不开种种“镇雄现实”的撞击,逃不掉一个写作者的责任与良知。我会一直写我的“乡下”,写我身边的每一个亲人。当然,写下这些的时候,我会无比幸福。
 (文字和图片均由昭通日报社通讯员尹马提供)
(文字和图片均由昭通日报社通讯员尹马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