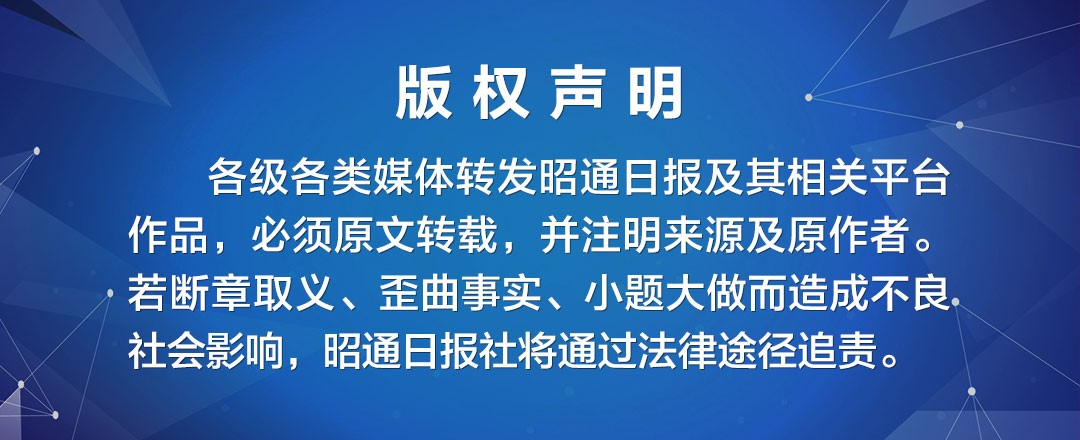2021-02-10 12:14 来源:昭通新闻网

那些年,年是从腊月二十三开始的。
“二十三,祭灶神。”爸爸妈妈在外工作,这类事做得有些敷衍。我妈早早起床,点上三炷香,对着回风炉作三个揖,再找个洋芋,切掉一半,把香插在洋芋上,供在回风炉上就行。
爸妈上班,我们几兄妹在家为过年作准备。我家的房子是爸爸他们单位分配的,据说最早是碎纸房。我爸找来包装板,把房子隔成两层,我和姐姐住楼上。包装板太薄,楼顶太矮,我和姐姐得弯着腰、踩着楼枕才能走到床边,如果不小心,包装板会被我们一脚踩断,脚也会被卡在包装板里。
腊月二十四,我们从印刷车间要来很多印废的纸,抹上糨糊,墙上、顶上一贴,整个屋子就亮了起来。我们叫这为“裱房子”。“裱房子”这种事只有哥哥能做,尤其裱屋顶的时候,一把椅子上面放个方凳,我扶着方凳,姐姐刷上糨糊,递给哥哥。哥哥踮着脚尖,把白纸往屋顶上贴,再用新扫把一刷,便大功告成。
裱好房子后,姐姐会带着我到街上买年画。那时的年画种类已经很多,毛主席像、十大元帅像、门神、财神、年画娃娃,还有明星画、风景画、国画等,我们家常贴的是国画、风景画,当然门神、财神也不能少,橱柜上边一定得贴一张毛主席像。这是爸爸的规定,没有人敢提出异议。
腊月二十六七,开始买肉买油买面买豆腐。那些年,这些东西靠供应,肉要肉票,米面要粮票,清油、豆腐当然也要票。攒了好久的各种票,就是为了让我们开开心心过个年。大清早,就到食品公司排队,有时候,排一天都买不到,只好第二天再去。这些票跟钱一样,非常珍贵,我妈根本不放心交给我们,一般都是她亲自去排队购买;偶尔会派遣姐姐先去排队,待时间差不多后,我妈再匆匆忙忙赶过去。
小妹嘴馋,又“撵脚”,一听我妈要去买肉,又哭又闹,说:“我要跟妈妈去食品公司买肉去。”我妈嫌她走路慢,让她待在家里。她不干,跳脚抹手,非要去。我妈顺手抽出根棍子,请她吃了顿“跳脚米线”,她这才老实了,边哭边求饶:“妈妈,我不‘胆’了,我不去了。”(她还小,话都说不清楚,把‘敢’说成‘胆’)那些年,每年她都要上演一场被打的“游戏”。我们在一旁做事,洗被子、擦地、褪锑锅上的黑烟,边干活边偷偷笑,幸灾乐祸!
腊月二十七八,就该炸“酥肉”、黄豆腐了。那时的“酥肉”,哪里舍得用整块肉,一般都是把肉、姜、葱等一起剁碎,搅在面粉里,加上水、盐和几个鸡蛋。一边用手捏,一边往油锅里放。头一碗“酥肉”,肯定被我们“偷偷”吃光。一年到头,也就是这几天可以吃上香酥可口的“酥肉”。我妈下班回来,还得检查一下,“酥肉”要炸得干一点,可以多放些日子,还省油。黄豆腐,是把豆腐切成大小均匀的正方形,同样用油炸干。吃的时候,可以煮上豌豆尖或者白菜,也可以红烧。水一煮,豆腐里包满了水,一咬,喷得到处都是,我们都叫它“喷水豆腐”。
过年,扣菜也是需要做的。宣威人善做扣菜,百合、蛋卷、白菜、韭菜根、南瓜、酸菜扣肉等,似乎所有的菜都可以夹上肉,垫上一层“树花”,做成扣菜。宣威人有个规矩:“过年三天不下生”,意思是过年那三天,不可以做生菜。所以扣菜也好,“酥肉”、豆腐也罢,至少得做够三天的用量。宣威人还有个讲究,要请“春客”。春节后的第三天,你来我家,我到你家,总得相互走动、聊天、吃饭,所以,我家里面那间屋子里都用松毛垫着,一碗一碗扣好的菜按品种用大碗盖着,放在青松毛上,等待取用。
青松毛当然舍不得花钱买,我爸会选个星期天,带上我和哥哥到山上“撕”。我爸借了一辆手推车,拉着往名叫花椒、靖外的地方走去。那时候雪真大啊,路两旁不知名的大树上挂满了晶莹剔透的冰凌条。太阳一出,冰凌条“噼里啪啦”往下掉,路过的时候得往路中间走。松毛上也全是冰,才一小会儿,就手冷脚僵,冷得不行,不过还是阻止不了我们去“撕”青松毛的热情,这可是为过年“撕”的青松毛。遇到天晴,雪融冰化了,就直接把青松毛从树上“撕”下;若是雪还没有融化,就得用镰刀砍,一枝一枝拖到手推车上,拉回家后,再慢慢将青松毛“撕”下来。
年三十事多,忙得中午饭都顾不上吃,随便吃点馒头面条便可。早上起来,我爸就得骑着自行车到几里外的电厂水库去买鱼。当时,鱼的品种不多,有一次,我爸买回一条大草鱼,有弟弟那么高,放进洗澡的大盆,尾巴都伸不直。买鱼回来,就该杀鱼宰鸡了。杀鱼宰鸡这类事,由爸爸亲自动手。我妈要再烧好两个炉子的火,一个煮鸡,一个煮火腿,回风炉则蒸各种扣菜。
扣菜不难做,难的是垫碗用的“树花”,我们叫“树胡子”。这种野菜跟人的胡子一样,长在深山老林,沾满了干松毛、杂草、泥巴,得一根一根地拣干净。这个活简单、累人,需要一百二十万分的耐心。哥哥姐姐没有耐心,只好由我上阵。我每天坐在家门口,一边晒太阳,一边拣。我把大簸箕放在腿上,从桶里抓上一把“脏”的放在里面,拣干净的就放进右边的小簸箕里。那时候年纪小,常常赢得几句过路人的夸赞。有一次,风大,把小簸箕吹翻,我拣好的“树花”全被吹到地上,等我追着把簸箕捡回来,地上的“树花”再次沾满了泥土、煤灰,再也吃不成了。还好,那东西长在山上,农民“扯”来就卖,一点都不贵。
姐姐爱吃扣百合,哥哥爱吃扣蛋卷,而我爱吃鱼。我可以把一条小鱼从背上开始吃,鱼肉剔得干干净净,留下头尾和整条鱼的骨头。吃鱼对我来说,哪怕是过年,也是一件很奢侈的事。那时的鱼大多是野生鱼,还没有人工喂养的鱼,买到的鱼都是水库边的村民打捞上来的。我总是小心翼翼地吃,舍不得丁点的浪费。
屋里撒上青松毛,一盘一盘的菜就放在松毛上,我们各自找自己爱吃的菜,席地而坐。
年夜饭开始了,第一就是吃鱼,“吃点鱼,年年有余。吃点长菜,常吃常在。吃点酒,常吃常有。”我爸总是一边说一边用筷子给我们夹鱼夹菜。我不会喝酒,连菠萝汽酒都喝不了,我爸专门为我买了一瓶杨梅露。酒喝过,鱼尝过,再吃一片长长的白菜,就可以自由地吃了,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当然,吃饭前还有三件事,一件是点香、供饭、给老祖人请安。另一件是喂狗。传说稻谷是狗系在尾巴上从海那边带过来的,做人必须懂得感恩,年饭得让狗先吃。还有一件事当然是放炮仗,“炮仗一响,黄金万两”。不过,炮仗对于我们来说,只是宣布我们家要吃年夜饭喽!
菜的品种没有过多的要求,除了长(白)菜、鱼、煮火腿、扣菜家家都要有,其他的随意。但有一条,宣威人最爱吃的“菜豆花”是不能上桌的,“菜豆花”是白事上的菜,过年和红喜事都不可以上桌,至于为什么,我也不知道,很多老规矩照着执行就行,哪有那么多为什么。长菜其实就是白菜。过年吃的白菜不能撕碎,要一整片地煮。最好是刚起花苞的菜薹,用清水煮上一大锅,最受欢迎。
吃过晚饭,要守岁,守到几点?没有强制性的规定,说是越晚越好,十二点以前是绝对不能睡的。饭菜撤下去,瓜子、水果就端了上来。没有电视,全家人围着火炉聊天、嗑瓜子、吃水果。弟弟还小,眼睛皮开始打架,头一点一点的,开始打盹。我扯扯他的袖子,说:“爸爸说了,不守岁就不给‘压岁钱’。”弟弟赶紧直起头,揉揉眼睛,说:“我不困,我没有睡哦。”过年我爸特别宽容,虽然同样指指点点,说我们这里不对那里不好,但绝对不会打我们。
“压岁钱”也从五分涨到了五角,一年到头,这是我们唯一的零用钱。我妈见我爸开始发“压岁钱”,忙起身进屋,把准备好的零钱拿来,给我们一人两角。就这样,我们有七角钱,这是多大的一笔财富啊!这个钱爸妈不管,由我们自由支配。姐姐的钱收得仔细,我从来不知道放在哪里。我的钱呢,常常压在枕头下面的草席底下。弟弟的钱则交给妈妈帮他保管,不然一定被哥哥“哄”来用掉。
年初一有很多禁忌,不让叫人起床,我们终于可以睡到自然醒。不过,很奇怪,年初一早上我们从来不会睡懒觉,接天连地的炮仗把我们“吵醒”,穿新衣裳、出门逛街的心把我们“跳醒”。吃过饭,哥哥姐姐就带着我们逛街去了。我把草席底下的钱拿出来,左看右看,拿了一角,放进毛线织的小钱包里,用别针别好,其余的钱收着,任由它“躺”在草席下面。
街上的人真多,挤都挤不过去,到处是维持秩序的警察。过年三天都要“耍龙舞狮”,还有骑驴、踩高跷的。我们跟着“耍龙”的人从上堡街走到下堡街,再到建设路、振兴街,怎么也看不够。龙头前有人拿着绣球,朝龙头左右摇晃,逗引那条长龙,一条龙要有十多个人才能“耍”起来。
拿绣球的是领队,抬龙头的人跟着绣球,后面抬龙身龙尾的人则跟着龙头“耍”了起来,从左到右,弯曲起伏,就像真的一样。狮子爬上另一只狮子身上,翻滚、跳跃,做着难度较高的动作。舞狮的人有很多是武术学校的,他们身手矫健,动作敏捷,叫人仰慕。龙,三四条不一,颜色各异。狮子一般就三对。踩高跷的人有各种装扮,各个朝代的人都能“聚”在一起,董永、白蛇娘娘、七仙女、穆桂英纷纷上场,凤冠高戴,水袖飘舞。
我牵着弟弟挤进人群,站在最前面,伸长脖子到处看。哥哥姐姐早就不见了,找他们的同学和小伙伴玩去了。“狮子”忽然张开大嘴,伸出个人头,对着弟弟做“鬼脸”,弟弟吓得大哭,我只好牵着他挤出来,花一分钱买了三块酸萝卜,抹上甜酱,酸甜辣都有,味道可口,弟弟吃得过瘾,早忘了那“钻出人头的狮子”。而我,损失了一分钱,才吃了一块酸萝卜,想了想,有点亏。弟弟说:“我还要。”我忙说:“不吃了,吃多了会‘拉肚子’。”
年初一要穿新衣服。五年级的时候,我的个子 “噌噌噌”往上长,用姐姐的话说:“就像施过尿素”,已经跟姐姐一样高了。那时候哪有什么羽绒服,仅有的一件棉衣,还是我妈每晚做完家务、改完作业,坐在灯下一针一针缝出来的,满满的全是针脚,摸上去就像长满了“虮子”。
我妈买了一块花布,请裁缝给我和姐姐各做了件一模一样的罩衣。我瘦、个子高,穿起来比姐姐“好看”,姐姐不服气,自己织了块围巾围着,暖和漂亮,硬生生把我“比下去”。好在,对美,我还“没有开窍”,根本就不在乎。我在乎的是裤子,我的裤子是姐姐原来穿的,裤脚都接过两道边了,已经掉色,呈灰白色,新接的还是黑蓝色,这让我很不舒服。我不敢说,怕被妈妈骂,一年能做一件衣裳已经不错了,裤子要等到明年才做。
过年,实在是一年盼到头的希望。
哥哥的新衣裳还没有钉扣子。年初一早上,吃过饭,我妈在洗碗。我们要出门了,哥哥偏偏不走,一个人坐在墙角的“松毛堆”上掉眼泪。没有新衣服怎么出门?好不好看无所谓,只要有就行,虽然会被别的孩子比下去,有总比没有好。我妈把碗放进筲箕里控水,一回头,看见哥哥还在哭,一问,为没新衣服哭呢!妈妈忙说:“别哭别哭,我几分钟就把扣子钉好了。”
我们老家的风俗,年初一不出远门,年初二到年初四这几天,一定要去老家的坟上给老祖人们磕头拜年。到了这几天,再远再忙,都得去。年三十忙,不得回家吃“年夜饭”的,这几天都要抽时间赶回去上坟拜年。我们很早就要起床,吃过早点,我妈把做好的各种供品及好酒带上,赶到车站坐车去老家。有时候,路上耽误了,当天返回不了家,就在婶婶大伯家住上一晚,顺便拉拉家常。爸爸的嫂子死后,上坟拜年更是成了一条不能更改的纪律。早些年,我妈带着我们去,这几年,妈妈老了,开始放手让哥哥带着我们去。
出了嫁的女儿是不能回家过年的。据说,要回娘家过年,必须顶个筲箕站在门后;回娘家上坟拜年更是大忌,“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不是自己家里的人了。我爸妈在外工作,思想开通,我家没有这种禁忌。但姐姐结婚后,还是严守这个传统,到了年初二才回娘家拜年。
因为姐姐,年初二也成了我们盼望的日子。姐姐来,总会带来很多好吃的东西,还会给我们“压岁钱”。结婚后的姐姐像个大人了,所有的礼物安排得妥妥当当,礼数也做得周周全全。我虽然跟姐姐一般高,却依然蹦蹦跳跳像个孩子。姐姐工作以后,就学会了织毛衣、做衣服,每年都要给我们织毛衣、做新衣服。我记得姐姐给我做的第一件衣服是一件格子线呢的,缝上根拉链,轻轻一拉,又合身又好看,只是左边的袖子裁剪的时候没有裁好,格子是歪的。不过,这丝毫不影响我对这件衣服的喜欢。
年初三早上,我妈会把屋里的青松毛扫掉。按照习俗,过年那三天不可以打扫卫生。如果年初三再不扫,就要等过了小年(正月十五)才能扫。那些青松毛,被我们跑出跑进,带得到处都是,实在等不到小年。扫完地,我妈就开始带我们走亲串戚。
城里只有一个亲戚,就是姨妈。姨妈家有六个孩子,大的三个已经工作成家,大表姐、二表姐也一起回到了姨妈家,一大家子人热热闹闹,吃饭打牌、下棋,丢车摔炮,很好玩。这两天基本都在姨妈家吃饭、玩。有时候也会到宣威的溶剂厂逛公园、猜灯谜、玩游戏。当时是溶剂厂最红火的时候,虽然厂里排出的脏水有一股臭鸡蛋味,但“花园式的工厂”让我们特别向往。溶剂厂小花园有各种花草、假山,还有孔雀、猴子等动物。看够了花园,再玩玩游戏,拿着奖励的糖果、铅笔、作业本,心满意足地回家。
过年,充满了快乐和喜庆。
那些年,我们住在爸爸工作的印刷厂,厂里有一个球场和一块比球场还大的空地,地上长满像蚊子的草。车间背后还有一大片柳树林,树林往前有一个大水塘,水塘上边有一个防空洞,防空洞里积满了水。
过年那几天,厂里的小孩子常常聚在一起玩“打死救活”“躲猫猫”等游戏,有时候也会在大柳树下面玩“过家家”。防空洞是我们想要探险的地方,可惜有一道铁栏,大门常年锁着。我们只好在防空洞两边的水泥斜坡上“梭”,这“滑梯”被我们“梭”得光溜溜、油亮亮的。
有了“压岁钱”,我们手里就有了玻璃弹珠、画片、水果糖、气球,我们头对头趴在地上弹玻璃球、拍画片、吹气球、“舔”水果糖,一天之后,新衣服就全是泥灰。过年不能打孩子,不然一年到头都要挨打,最多只能骂几句。这么想想,过年真的是我们的“天堂”。
年初五以后,年就算过完了,我们的“好日子”也该结束了。我妈照样叫我们起床、挑水、洗菜、写作业。趁爸妈不在家,我们几兄妹在家里数“压岁钱”,比比谁有钱。我哥手“散”,“压岁钱”已经没有了。而我,才用了两角钱。我心满意足地把钱继续收在草席底下,等到开学后课间休息时,到校门外,花一分钱买根长酸菜,一缕一缕撕着吃,还可以分给要好的同学一起吃。
“年”里“剔”得干净完整的鱼骨,山里去“撕”来的青松毛……统统分散在松散的日子里,成了对那些“年”的回味。

崔玉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