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新闻 2021-01-27 10:02 来源:昭通新闻网
”
陈永明,昭通永善人。云南省作家协会、中国散文学会、中国诗歌学会、云南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在《散文选刊》《边疆文学》等发表作品。出版作品集《心灵的守望》《故乡那头是乡愁》等7部。云南文学院2014作家班学员。现供职于永善县文联。
”
故乡记(组章)
陈永明
我的衣胞之地
村庄,是我血脉流淌的衣胞之地。我的童年和记忆,是从那个小地名叫花楸坪的村子开始的。顾名思义,那里曾经是一个山水环抱、树木葱茏的地方。
村庄是恬静的,故乡是恬美的。在村庄的炊烟里,和伙伴们一同游玩和嬉戏。在故乡的风景里,我们一天天长大,带着记忆中的春花秋月离开故土,带着梦幻中的夏雨冬雪告别家园……
我渴望,回到儿时的记忆,回到如今我回不去的故土和家园。
从乡村走进县城,所处的环境更大了,我的空间却很小。早些年,曾经蜗居在机关办公室一间只能放一张床的杂物间里,读书写作打发时光。在那个空间里,我读到了许多过去没有读过的“闲书”。有一篇题为《劝种树说》的史料曾记载:“历史上的永善,旧为夷疆,处万山崎岖之中,人稀地广,荒僻特甚。自雍正之初改土归流,始沾王化。越数十年,地渐辟,人渐聚。然而山溪之树木屋之、薪之、炭之,用莫能尽,翳翳焉,丛丛焉,有行数程而不见天日者矣。由是虎豹依之为室家,盗劫缘之为巢穴,昏黄而野兽入城者有之,冲途而颠越行旅者有之。”
原始、生僻的文字,是苦涩的记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出生的人,至今朦朦胧胧,对那段岁月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追忆,毕竟是不谙世事的童年,所有的往事仍旧是美好的。水边的村庄,树上的村庄,田园美景的村庄,是我最初的记忆。当年伐木烧炭、大炼钢铁,砍了很多的树;当年开荒种地、“放卫星”,村里的老梨树也没逃脱厄运。记忆中的老梨树被几个比我父亲还精壮的人放倒在地,村里的几个木匠则三下五除二,把老梨树做成了几辆手推车,拉土运石。那年月,开荒种地成为一种时尚,刀耕火种成为一种速度。种田,远没有种地那样清闲。后来,村里说话管用的领导说了一句“革命”的口号,村里的那一大片水田,就无偿变成了隔壁村的地盘了,本村的几百号人便“靠山吃山”、上山“开荒”种地。时至今日,老家房前屋后的水田,都是外村人继续耕种着。老家那个院子,成了名副其实的“孤岛”,进出家门的路还得每年花钱租用。曾经“靠水而居、在水一方”的老家,仍旧深居在田的中央。
随着时间的推移,集体山林的树木渐渐稀少了。做饭、烤火要烧柴都成问题,特别是每年十冬腊月,家家户户都得备过冬的烤火柴,我还跟随父亲上山砍过柴、刨过树蔸,为过年烤火作准备。老家的山水,村庄的容颜,犹如我一辈子牵挂的故乡的山风和明月,一天天地在改变着。天长日久,我们无需更多地去拷问:谁的过失,谁的责任?
在远逝的岁月里,父亲也带着我们在房前屋后种了一些树,一些可以遮荫添绿的大青树。虽然,父亲不知道绿色与青春有关,不知道绿色就是生命律动的另一种形态,但他知道,绿色与家园有关。让自己的家园充满绿意,那是一道不错的风景。
如今,老家的山水,满目青山,过眼白云,溪流淙淙,依旧是我的生命所在!
父亲的“龙抬头”
在乡下,元宵节一过,年就算过完了。接下来,便是城里人和乡下人都很在乎的日子,农历二月初二的“龙抬头”。
俗话说“龙不抬头,天不下雨”。龙,是民间祥瑞之物,又是“和风化雨”的主宰和象征,人们祈望“龙抬头”兴云作雨、滋润万物。据说,这一天,天上主管云雨、冬眠的龙王,被隆隆的春雷惊醒,便抬头而起,降甘露于人间。其实,农历二月初二前后,是廿四节气中的惊蛰,之后,雨水也会渐渐增多起来。春季来临,万物复苏,一年的农事活动如火如荼,农村正式进入繁忙的春耕播种时节。在民间,有“二月初二剃龙头”的说法,认为这一天剃头,可以给人带来“红运当头、福星高照”的好运。
记事时,每到二月初二这天,父亲都要请住在隔壁院子、曾经在部队里当过吹号兵的二伯到我们院子,帮着父亲为我们三兄弟“剃龙头”,然后再给父亲剃头。那时家里穷,没条件拖家带口进城去理发,多数人家都是自己买了剃头刀,在家里请人剃头,或者到隔壁人家一起剃。直到我上初中,每次鬓角头发盖耳了,才去县城老四街口的“金江”理发店,花二角五分钱,剪一个小平头。
父亲常说:“二月初二‘龙抬头’,剃了‘龙头’好跳‘龙门’。”每到那天,父亲总记得烧上热水,亲自主持为我们三兄弟剃头,三个姐妹则用剪刀象征性地剪去一点头发或者修修剪剪,意思不外乎希望我们六个兄弟姊妹都能健康成长,好好读书,学点真本事,将来有个好出息。
记得,我在上初中的第一年,二月初二正好是周五,学校下午不上课,我早早地去排队、理发、回了家。那天天气正好,暖洋洋的,父亲心情好,他说他也想剃个“龙抬头”。热水烧好了,同院子的大伯正好有事出去了,隔壁二伯也不在家,父亲洗好头,便摸索着自己剃头。
父亲身体不太好,都是那些年喝酒喝出的毛病。那些年,没粮食煮酒,父亲多半喝的是甘蔗皮为主制作的“榨皮”酒,除了喝出了胃病外,还喝出了干咳的毛病。没钱医治,就喝土法偏方汤,还常年离不开止咳的西药片“麻黄素”。头剃到一半时,父亲忍不住一阵干咳,不小心耳朵旁的鬓角便划出一道血痕,瞬间,一串血珠珠像蚯蚓似地爬上了父亲的脸。为了继续剃去另一半湿漉漉的头发,父亲便叫我为他剃头。
我从小就怕剃头。小时候要剃头时,父母多半要给上一两分钱,或者煮个鸡蛋哄着,我才能在哭哭啼啼中剃完头。看见父亲叉着八字形的腿,在自己粗糙的劳动布裤腿上“唰唰唰”地荡刀子,拿着光亮闪耀的剃刀,心里便一阵阵发紧。特别是当剃刀在自己头上“嚓嚓嚓”地游走,头发在火辣辣的疼痛中被刮完时,后背就一阵阵发凉,好不容易才熬过剃头的时光。
虽然心有余悸,但碍于父命不可违,也不能看着父亲带着一个“阴阳头”下地干活,我便抖手抖脚拿起剃刀,要往父亲头上下刀。父亲说:“别忙。”他叫我从灶房里找来一条吃饭用的矮板凳,父亲则坐在草凳上,要我跪在矮板凳上为他剃头。父亲说:“男人的头女人的腰,何况老辈人的头,晚辈是不可以随便碰的。发肤受之父母,得有尊长之分,不可坏了规矩。”
本来就很胆怯、心虚,被父亲这么一说,自己心里就更紧张了,还得跪在板凳上,接着父亲摸索着剃了半边的头发,继续为他剃个“龙抬头”。
左手抚着父亲的后脑勺,拇指和食指交替着绷紧他头上松松垮垮的头皮,试着把稀稀疏疏的黑发和白发从头皮上刮下来。只听父亲嘴里“咝”的一声,头微微扭了一下,糟糕,头皮上一块表皮翻了起来,随即浸出了红红的血。父亲说:“别怕!”随即拿过剃刀,在他大腿裤子上一上一下、一反一正荡了几下,又在腿上示范着教我如何下刀剃发。父亲说:“心要静,刀背平靠头皮,微微抬起,把握好刀口和皮肤的角度,上下平着刮就行,切忌不能左右拉锯子似地移动刀口……”父亲越说,我自己心里越慌。父亲鼓励我大胆地下刀,“不就是剃个脑壳,未必还有‘背一背、挑一担’累人?”听了父亲的话,我大起胆子,几乎是闭着眼睛,跪着在父亲松弛的头皮上刮下了一绺头发。父亲说:“就是这样的,慢慢地就会了。”父亲半边头上的头发快要被我剃完时,跪在膝下的小板凳偏了一下,我酸软的腿也不由自主地晃了一下,顿时,父亲右边太阳穴旁一小块皮肤又翻了起来……我吓得不知所措。父亲却嘿嘿一笑,安慰着我,风趣地说:“没啥大问题,收音机里不是在说,不流血流汗哪来的革命成功?”末了,父亲还说,我们在农业上种庄稼、你们在学校里读书,都是这样的道理!我暗自庆幸,幸亏真的没啥大问题!这时,同院子的大伯赤着脚、背着牛草回家来了。他既为我解了“围”,也为父亲清理干净了头上没剃完的发,圆了父亲剃“龙头”的愿望。
是啊,不流汗哪来的成功,不付出哪来的收获?怀揣着父亲的教诲,直到今天已是四十多年了,那剃头刀虽已锈迹斑斑,淡出了视野,但生活的剃刀依旧锋利,“龙抬头”的美好祈愿仍在心底继续,那段抹不去的记忆仍在继续,父亲剃“龙头”的美好向往和家风良训仍在传承中继续。
四十多年,每年我都会在心里为父亲剃一个“龙抬头”。
母亲的“社保卡”
新年刚过,离春节还有一段时间,我照例在周末回乡下老家,看望80多岁的母亲。
那天,刚进家门,母亲便神神秘秘地翻出一样东西:社会保障卡。母亲说,我也有这种“卡”了,可以看病、领养老金、领老年补贴……应该是和以前的“存折”一样。母亲叫我把它带回城里,在银行自助取款机上帮她看看,原来那“存折”里的钱还在不在、转存上去没有,现在这“卡”上有多少钱了。
言谈间,母亲那爬满皱纹的脸上,是满满的自豪感。
是啊,在如今“卡”行天下的年代,“卡”似乎都成了身份的象征。诸如储蓄卡、信用卡、购物卡等。虽然我不赶时髦,除了一张必须的身份证外,也有几张必须的公务卡、工资卡和社保卡。刷卡消费,也成了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一种时尚,也是发展的必然趋势。
原来,母亲在几天前感冒了,去村上的卫生室请医生看病,打了针,开了感冒药。母亲是带着“卡”去的,“新农合”报了账,自己交了20多元钱。母亲接着又补充说,那是她自己平时的零用钱,都没问子女再要钱了。是啊,母亲也有自己的“小金库”了,这是在计划经济年代,想都不敢想的。
母亲是土生土长的农村人,生于1935年,也就是毛主席写《七律·长征》那年的4月出生的。母亲的老家在金沙江边的永善县务基镇锦屏村海口村民小组,老地名乌木寨。外婆刘李氏养育了母亲4姊妹,母亲为老四。母亲7岁多时便随外婆逃难到了现在居住的新拉村柏杨村民小组,被她早年迁居在此的大叔、大婶收留,并挤出一间“牛圈”供外婆和母亲临时居住,母亲则帮忙放牛、割草,做些临时家务。1950年4月永善县城解放后,当时16岁的母亲便被“抢亲”到了同村的胡家桥,做了给我生命的母亲。
母亲说,她从未见过自己的公婆。当年,我的父亲和伯父兄弟两人,住在一个四壁透风的茅草棚里,靠给大户人家放牛、帮工为生,缺吃少穿是常事,一条好一点的长裤子,父亲和伯父出门轮着穿,日子十分艰难。父亲成家后,伯父另立了门户,不久又张罗着,把在邻社周家当丫鬟、做“厨娘”的伯娘“抢”了过来。那以后,父母和伯父有了他们各自的归宿。好不容易熬过了“三年困难时期”,父母便开始改造破烂的茅草屋。我出世那年的10月底,正好是老家那排土坯房快要竣工的日子,早上都在为帮忙修房的乡亲做饭的母亲,下午便在家里坐起了“月子”。母亲常说,我来得正是时候,新房子修好了,续“香火的”我也降生了,让父母感受了“双喜临门”的喜悦。第二年,伯父、伯母也在相邻的地方,门对门,并排修起了3间土坯房。上下空着的两排,伯父为大,选了上排,修了自己的厨房、畜厩,父亲则在下排修了两层的畜厩,一个自然的小院就形成了。20世纪70年代初,衣食问题解决了,加上父母的精打细算、辛勤劳作,家里生活条件慢慢好了起来,父亲和伯父商量着,在城郊干河村的巫家瓦窑买了小青瓦,两家人都把茅草屋顶换成了瓦房。然后,在临昭永公路一侧选好“向山”的方向,修了一道共用的“朝门”。从此,一院两家、情同手足、和谐相处,小日子一天比一天好了起来。
如今,这个院子经历了将近60年的风风雨雨,依旧温馨如故。父亲36年前最先“走”了,之后伯父伯母也相继“走”了,伯父家里的堂姐早年远嫁他乡。如今,84岁的母亲,依旧同最小的兄弟住在这个四世同堂的老院子里。
年迈的母亲常说,岁数大了不管事了,有兄弟一家操持家务,自己也轻松多了。在母亲的眼里,兄弟是头脑灵活、孝敬老人、能吃苦耐劳的。他从铁匠干到石匠,从种包谷、洋芋、稻谷,到种核桃、花椒,从养鸡养鹅养猪,到就近打零工……靠自己勤劳的双手,在我们6个弟兄姊妹中率先致富,将父亲修的两层畜厩改建成水泥砖房。3年前,又将父亲留下的那排曾经很风光的大瓦房改建成了水泥楼房,还做了屋脊装饰。兄弟自己买了农用三轮车,宽敞的户间道把院子和昭永油路连在了一起,出工下地,不再肩挑背扛,作物收成装在车里方便快捷地开进院子。长大成人的侄子、侄女们,有的在浙江省固定务工,有的在昆明市安家落户,办起了洗车场,有的开起了公司,都买了小汽车。
母亲常说,现在的政策就是好啊,城里有的乡下也有了,乡下有的城里还不一定有。何况,乡下比城里还清静。也难怪,母亲以往进城总待不了几天就急着要回“住惯的山坡不嫌陡”的乡下。母亲嘴上虽说,自己赶上了好时代、过上了好日子,死了都值得了。但是,每每想起早逝的父亲,母亲心里也是满怀惆怅地感叹:要是你爸爸在就好了!
曾经,母亲最大的心病,总是担心自己过不了80岁那个坎,当初是我借“算命先生”善意的谎言,说母亲有九十六岁的寿命,才慢慢说服了半信半疑的母亲。如今,岁数越大,母亲反而看开了,心态也不再为“身后事”纠结。
坐在老家门前的屋檐下,母亲像把玩宝贝似的,抚弄着手里的“社保卡”,隔着几坵金黄的稻田,静静地细数着公路上过往的车辆和奔波的行人。母亲对眼下的好日子格外珍惜,也很满足、很惬意。按母亲的说法是:过去“吃不像吃、穿不像穿的”都过来了,何况现在每月有“老年保”“高龄补贴”,还用上了手机、饮水机、电视机,重孙绕膝、衣食无忧,只管细数着光阴,享受天伦之乐。
是啊,母亲这一生坎坷曲折的经历,何尝不是一段历史的见证,见证了新中国成立的庄严时刻,见证了国家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发展历程。老家那个普通的农家小院,从无到有,从茅草屋到小洋房,何尝不是一段中国农村发展的缩影呢?
地里的“落花生”
白露一过,高山上的核桃可以大量地吃了。和核桃一样,老家的花生也开始采挖了。
进入农历七月,天气渐渐凉了起来,有点秋风秋雨的味道,头脑里也会常常梦见去世的亲人,梦见八十多岁的母亲模模糊糊交代一些事情,梦见年轻的母亲风风火火背一个抱一个、带着我们兄弟姊妹捡花生的过程……
那时的乡村,没有幼儿园或者学前班,只要我们的右手能够摸着左耳朵便可上一年级读书了。小时候,我只能偏着头才摸得到耳朵时,父母便让我背着花书包、装上自制的算数教具——许多的包谷秆“小棒”,接过母亲从灶台上炕好的干花生,一路哭着去了学校。星期六不读书时,就跟着母亲下地,母亲会刨开泥土,看看土里白胖胖的花生长大没有,顺便摘下一两颗给我们解馋。我还记得,在假期里,坐在父亲的人力“花轮车”上,让他拉着花生藤和我,一起去白沙田家坡水磨房打“猪草”的日子……
母亲没文化,讲不出啥道理,她只知道盘田弄地不流汗不行,不辛苦付出就没有收成。那时年幼,不懂事,也没读过作家许地山写的《落花生》。后来,读完小学保送进了初中,知道了《落花生》阐述的意义和内涵,懂得了做人做事的道理。这些,于母亲而言是高深的。母亲虽然知道“根根胡须钻泥巴,自造房子自安家,地上开花不结果,地下结果不开花”的谜语,但她不知道花生为啥花开枝头却钻进土里结果,不知道花生为啥还叫“落花生”……在母亲眼里,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儿孙绕膝时的快乐时光;全家团圆时,就着香喷喷的炒花生,说一大堆理不完的家长里短或回味意犹未尽的往事。
老家离城不远,父亲去世得早,母亲在城里住不惯,常年和弟弟一家住在乡下。每逢周末,我都要尽可能地回去看看。
农历七月十三,是周末,也是老家习惯过的“七月半”,与清明时节扫墓祭祖一样,我是必须回去的。
刚到家里,母亲正和弟弟一家围在一起摘花生。沿着院子边已经堆积了一大圈打成捆的花生藤,还有一大背连藤带果的花生没摘完。
弟弟催促弟媳做饭,他作帮手。我坐在母亲身边摘花生,像往常一样听母亲说话,尽管她那城里的儿媳、孙子、重孙没能一道回去,但母亲心里还是很畅快的,看得出她是高兴的。
母亲说,今年闰六月,干旱久了,收成比不上往年。今年种的花生不多,大约有三分地左右。除收到几大捆偶尔还带着些小黄花的花生藤外,没收到多少籽粒饱满的花生。
临走时,弟弟装了满满一大袋先前摘下的洗得干干净净的鲜花生,母亲非叫带上不可。母亲知道,城里可吃的很多,但没有老家的那种浓浓的“家”味。我知道,这“地下结果不开花”的“落花生”,装满的是一份牵挂,是理不完的家长里短,是“送出家门回头望”的乡愁。
唐诗宋词里的故乡
穿越时空,与古人对话,聆听他们对故乡的吟唱。
李白有《望天门山》:“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回。两岸青山相对出,孤帆一片日边来。”白居易有《忆江南》:“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孟浩然有《过故人庄》:“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王维有《山居秋暝》:“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其实,像这类描写故乡、描写村庄,讴歌山川河流、人文风情、田园风光以及花草鱼虫等的诗篇,比比皆是。我们可以踏着古人的脚步,探寻“一江碧水,两岸青山”的美景,领略那“晨光映照岸边的红花,比熊熊的火焰还要红,清风吹拂满江绿水,就像青青蓝草一样绿”的乡村画卷;可以体验乡村做客的“赴宴图”;描一幅“青山,绿树,村舍,场圃,桑麻,菊花”点染的画面;绘一幅“明月青松、山泉清流、浣女戏水、渔舟晚归”的村姑“洗衣图”。
古人眼中的乡村是诗意的,也是我魂牵梦萦、叶落归根的处所。杜甫《江畔独步寻花》中“黄四娘家花满蹊,千朵万朵压枝低。留连戏蝶时时舞,自在娇莺恰恰啼”。描绘了农家房前屋后的小路上,鲜花盛开,花团锦簇,惹得彩蝶飞舞,娇莺吟唱,路人心旷神怡、流连忘返;杜牧《山行》里“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生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展现了秋冬时节红叶开得正艳,忍不住停车驻足观赏这一独特的风景。
这些意境,把自然景色与友人热情融为一体,表达了人与自然的和谐之美,这正是我们现代人正在倾力打造的“秀水、青山、白云、蓝天”,也正是我们当代人梦寐以求的乡村典范和“世外桃源”……
 来源:昭通作家
来源:昭通作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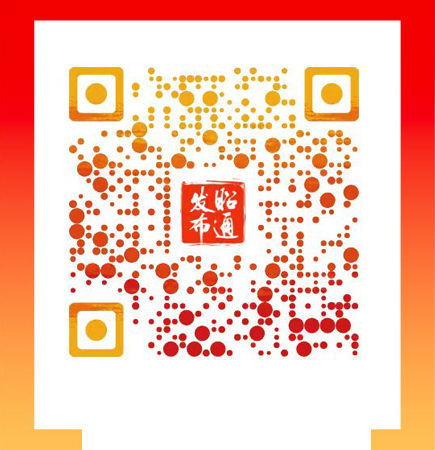

联系电话:0870-2158276
登报作废:0870-3191969
联系邮箱:ztnews@163.com
主办:中共昭通市委宣传部、市政府新闻办;承办:昭通日报社;Copyright © 2017-2028 昭通报业有限责任公司
新闻爆料、涉未成年人举报、涉毒及有害信息举报:0870-3191933 举报邮箱:ztnews@163.com,涉毒举报,疫情求助
登报作废:0870-3191969,流量造假、黑公关、网络水军举报电话:0870-2159980
昭通市“打假治敲”举报电话:0870-2132590,举报邮箱:305906736@qq.com,举报地址:昭通市昭阳区公园路45号市委宣传部(市委大院内)
滇ICP备19003243号-3 ;云南省公安厅备案号:53060203202019;互联网信息新闻许可证编号:53120180014;互联网出版许可证:(总)网出证(云)字第002号
本网站法律顾问——云南意衡律师事务所 赵文律师,未经昭通新闻网书面特别授权,请勿转载或建立镜像,违者依法必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