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08-12 09:14 来源:昭通新闻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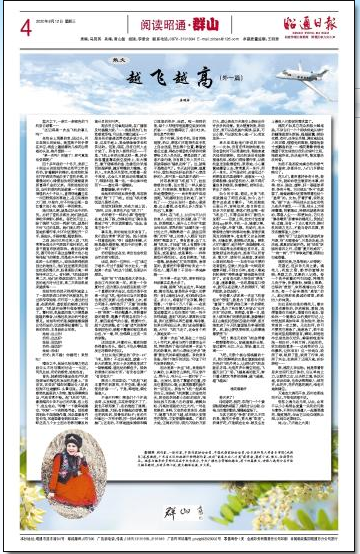
蓝天之下,一架又一架银色的飞机穿云破雾……
“还记得第一次坐飞机的事儿吗?”
在阳台上观景的我,扭过头,问正在梳头的姑姑。她捏梳子的手停在半空,梳齿上缠绕着的几根花白带卷的头发,格外显眼……
“第一次吗?别提了!那可真是活受罪呢!”
四十多年前的一个冬天,我那二十刚出头的姑姑和将近花甲之年的奶奶,穿着臃肿的棉衣,在咸阳机场东打听西找寻地办妥了登机手续,怀着激动的心情要去陕南安康看望我那喜得千金的父亲。用我姑姑的话说,当时的咸阳机场就像一个孤独又恓惶的大个子巨人,直愣愣地矗立在一片四野荒凉的草地上,在它冷清的大门前、怀抱内,时不时会出现一些扛着大包小包、难民一样的乘客。
她们娘儿俩,就是这队伍中的队员。办好了登机手续后,她们就坐在停机坪旁耐心候机。苍茫的天空上,除了偶然飞过的一两架飞机,就是时不时飞过的鸟群。她们娘儿两个,紧紧地抓着行李,时不时还要松开一只手,扬起头,手搭凉棚,翘首期待。
之前,她们已听过来人说,飞机常常会因为天气原因不准时到达,或者干脆宣布航班取消。遇到这种情况,最可怜的不是这些携带大包小包等待起飞的乘客,而是在兴冲冲地等在那一头的接机人,因没法获得航班到达的准信儿,他们往往要来来回回往机场折腾几次,盼星星盼月亮一样等待来访之人。有时候,飞机延误到第二天,他们还得返回城内,找个便宜的地方对付过夜,第二天再回机场来继续等……
姑姑和奶奶那天很顺利地登上了一架苏联进口的伊尔民航客机,挤过那窄窄细细、仅仅容一人通过的过道,在硬邦邦、直板板的座椅上刚刚坐好,飞机就开始滑行准备要起飞了。霎时间,机舱里四面八方满是轰隆隆的噪音,比拖拉机发动的气势还要足。姑姑和奶奶是肩膀碰着肩膀比邻而坐的,说话都得扯着嗓门。而我的奶奶,本身就有点耳背。
姑姑:这么吵!
奶奶:这还好?
姑姑:没说好!
奶奶:谁说好?
姑姑:没谁!
奶奶:我不睡!你睡吧!我想吐!
嘈杂之中,姑姑已经没精力把这段牛头不对马嘴的对话一一纠正。何况此刻,奶奶的感觉,姑姑也有。
首先,她感觉好像坐在生产队那烧柴油的拖拉机发动机机盖上,“突突突,突突突”强烈的震动令人肌肉控制不住地颤抖、头晕目眩。其次,感觉机舱里的人和物,填充得满满当当,气流非常不畅。起飞后的飞机,像是飓风中身不由己的风筝,忽上忽下,忽左忽右,“呼噜”一下像旱地腾空,“吭哧”一下若探海寻鱼。姑姑感觉到肚子在隐隐作痛,耳朵里像有汽笛长鸣,耳道里像有蚂蚁巡回……耳畔还有几个女士因为恐怖而爆发的高分贝的尖叫声。
服务员立马拿起话筒,在广播里及时提醒大家:“……旅客朋友们,如您感觉耳鸣,可以张大嘴巴减压……”服务员的普通话带有或多或少的乡音,这在平地上,是会被偷偷学舌和笑话的。但是,现在,没有任何人去计较了。所有的人都很听话——于是,飞机上突然出现这样一幕,好多旅客僵直靠在航空座椅上,张大嘴巴,像干涸竭泽的鱼,也像因为饥饿而挤眉弄眼、龇牙咧嘴的大嘴兽。有的人,本来是牙关紧咬,死憋着一股子难受,这会儿只顾启动张嘴减压了,哪里料到,嘴一张,一条白练冲泄而下——直吐得一塌糊涂。
颠颠簸簸,终于停下。
姑姑和奶奶彼此搀扶着,形容狼狈地“爬”下了飞机。初坐飞机的喜悦劲儿荡然无存。
姑姑双腿发软,站在大地上说:“妈呀,以后,我再也不坐飞机了!”
奶奶粽子一样的小脚“噔噔噔”在地上跺了跺,仿佛在印证“确实是落地了吗”,然后紧跟着说:“谁坐,谁是它孙子!”
事实是,我的姑姑后来食言了。我们因此常常“笑话”她。她小姑娘一样羞涩起来:“呀!谁能料到嘛,大路是越走越宽畅,现如今的世事,完全不一样了嘛!”
奶奶假如还在世,肯定也会收回当年的那句狠话。
话说,我的一位师长、一位“读过万卷书、行过千里路”的文社长,一提起第一次坐飞机这个话题,也是谈兴颇浓。
他的“初飞”体验是在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后的第一年。那是一个仲夏时分,因为要从古城西安赴银川开一个重要的学术会议,也因为是平生第一次坐飞机,他对自己当天的着装也是记忆犹新:白色的确良上衣,派力司裤子,咖啡色开了“天窗”的凉鞋——这是一双圆圆的包头凉鞋,中间一根“脊梁”一样的鞋鼻子,串联着环绕的鞋带,鞋鼻子两侧各有四个小孔,像四扇透气的小窗。酷夏时分,脱下这双凉鞋,有“小窗”透气的脚背是深棕色的,被鞋子覆盖的部位是肉白色,乍一看,呀,仿佛脚上还有一双肉凉鞋。
话说回来,仲夏时分,看家狗都热得直吐舌头。猫们,不住从喉咙里发出对酷热的抗议。
文社长他们乘坐的“伊尔-62”飞机,更热!不过份地说,就像一个巨大的蒸笼,把五十多名乘客变成了一锅软踏踏、湿哒哒的鲜包子。燥热的乘客们纷纷打听:“有没有空调?”“有没有水?”
乘务人员回答说:“飞机起飞前本着节约的原则,不开空调,请大家使用折扇……”。于是,哗啦啦,满仓摇扇人。
不扇不行啊!乘客们个个汗流浃背,头发粘湿,实在热得受不了了,就也不顾形象了:有的挽起了裤脚,露出膝盖、大腿;有的撩起衣前襟,露出肥肉形的、排骨形的肚子;有的不时拿出一方布手绢,按一按水淋淋的脑门;还有的,不停地搓抹脖颈和胸口滚滚的热汗、油泥。唯一相同的是,每个人呼啦呼啦摇着空姐发的纸折扇……话也懒得说了,省口吐沫。那也是节约啊!
那个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网络链接,所以,乘客们不能预先在手机上自由选座,想坐哪个位置,靠窗或者近过道,得在办理登机手续的时候要给工作人员先说。要是说晚了,或者不谙内情,没有跟工作人员开口,那就得被动“随机安排”了。这,就等于是赌运气了。冬天还好说嘛,盛夏时分,假如身边恰好坐的是个心宽体胖的人,那可是一丝风都不透的……
好容易熬到飞机起飞了,丝丝缕缕的白雾,仙女驾云一样从座位上方、行李架侧,散散淡淡、悠悠然然地慢慢喷出……尚未等到汗体凉透呢,飞机播报到达目的地了,该下机了……文社长当时一直在心里琢磨:这么遭罪,还有那么多人想坐飞机出门,真傻!
那时,在飞机上,认识与不认识的客人,相互讨论的话题,除了“同志,你是哪里人,做什么工作的”和就当时知识、学界的热门话题引发一些讨论之外,稍微熟悉一点,就会压低嗓门打听飞机上的客人入厕后“拉的粑粑”哪里去了。更有甚者,坐了几趟飞机后,才知道飞机上有厕所(难道没有听空乘人员的播报吗?或者紧张,或是羞怯,或是晕机……种种原因不得而知)。还有的乘客,飞机一落稳,就急急忙忙找寻厕所,急得紧的,直接把行李嘱咐给身边一个陌生人,撒开脚丫子没命一样地奔跑……
关于第一次坐飞机,我听到的各种故事实在是太多了。
的确,搭乘飞机去远方,旱地拔葱,腾空而起,曾是很多中国人的梦想!有《山海经》为证,有《西游记》为证。多少人,希望肋下生双翼,腾云驾雾,一个筋斗十万八千里……在我童年时,曾和家属院里的小伙伴们,紧追着蓝天上拉白烟的飞机一阵子欢呼疯跑,直到飞机钻入厚厚的云层里,我们还要仰头再巴望着,等待着,如果它再钻出云来,我们还会跟着狂跑,大叫!飞机飞走了,还会有个别人原地发呆……
我第一次坐飞机是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感受与两个前辈完全不同,特别是听了他们讲述第一次坐飞机的故事后,我内心萌生出许多“晚辈”新生代的幸福优越感。我的亲身体验,用时下流行的话说:“印证了时代发展的脚步。”
因为是第一次坐飞机,我是格外认真的,认真到怎么乘机,可以穿什么、带什么、吃什么……都打听了一番。出发时,首选了靠窗的位置,按压住喜悦的心情,认真观察着机舱外的一切变化。那些与飞机一起奔涌的白云,涂染在飞机侧翼上的金色阳光,那些忽然间渺小如蚁的城市,细如丝线又四通八达的道路,蜿蜒如蛇、闪亮如银般的大江大河,一时在我眼前、身畔,又忽然在我身后、在脚下,随着飞机的飞越,城市烟火变得苍茫混沌,又变得清晰逼真。广袤的大地,辽阔的天际,明灭闪烁的万家灯火,都让我在万米高空上萌生出许许多多的诗意。更为惬意的是,收回目光,我可以在机舱内阅读、品茶,可以小憩,可以放松身心地一门心思发发呆……
我无法体验他们所说的旧时光——比如,没有宏伟的航站楼,也没有登机时可以贯通机体、帮旅客遮风挡雨的廊桥。因为机场没有挂梯接通机体,旅客们得挎着行李,从候机室走到舷梯登机,笨笨地、小心翼翼地攀登上去,常常夏天一身汗,雨天一身水。天气恶劣时,还曾见过个别乘客在风里追帽子、追假发……让挤满舷梯、急切登机的人,顾不得打量自身的狼狈,扶着梯栏,前仰后合,笑出了泪花……
如今的中国,据说,光是飞机场就建设了两百多座,如今,这个数字还在逐日攀升。飞机的航班云里云外,穿梭往来,每日排有三百多万次航程,乘客们想坐哪一班飞机出门,只需启动我们“新四大发明”——百度上网,找支付宝或者其他app软件,手机一点,随意订票,点击付款,尽情飞翔。机场内,有为乘客惜力惜时的移动电梯,有惜步兼观光的摆渡车,有连贯又安全的廊桥,无缝连接,直接抵达机舱。候机大厅内餐厅、地方特产、服装鞋帽、化妆日用品等生活配套应有尽有。在宽敞舒适的机舱内,旅客可以听音乐、看大片、读报刊、品航食,享受贴心周到的服务……如有行动不便的老者登机,空乘人员会第一时间前来嘘寒问暖,不到五分钟,连老人落地的轮椅和“特殊通道”路线都给安排好了。还有些无家人陪伴的“候鸟”儿童,逢寒暑假,一张机票揣在口袋中,就可以在空乘人员的照顾下,“顺利回家,各找各妈”。
听老辈人讲述第一次坐飞机曾经的“恓惶”,就是为了感恩今天的“富强”!顺带讲自己第一次的乘机体会,是为了给后辈儿孙留点“比对历史”的谈资。我希望,有朝一日,能有人续写我们的乘机故事,就像镌刻在《山海经》《西游记》里的寻梦,逐日演变成了今天民富国强后幸福的圆梦。那,就让梦想更绚丽,让故事随着梦想飞!
飞吧!勇往无前的飞机会带着一颗颗澎湃的心,穿越高高的云层,掠过黄河、长江、天山、草场、塞北、江南……
飞吧,无数个被白鸽唤醒的十月,我们把鲜艳的五星红旗披挂在银灰色的飞机外壳上,让成队的飞机在鼓乐齐鸣、礼炮声声中腾空而起,飞越天安门广场,飞越高高的蓝天,牵引着无数双寻梦的眼睛,越飞越高,越飞越远!
槐花静静开
春天来了!
待迎春花、桃花、杏花们一个个黄颈粉颊地热闹罢了,槐花才以白苞、白袍、白如雪的散淡,慢慢地登场了。
与其它那些“争春”的花儿不同的是,槐花不争春,更无意“取宠”。所谓开花,仅是顺应生命、顾及尘世上善良人们殷切的需求罢了。
槐花不如其它花朵那般大肆渲染,不似它们一个个闹哄哄地从绿叶的罅隙里探头探脸、描眉画鬓、顾盼生辉,有时,还伸出手脚,调皮地扯扯人的衣襟,碰碰他的脚板,搔搔他板寸或飘逸的发……槐花静静悄悄地隐匿于犹如绿色仪仗队的绿叶之间,细碎地存在,淡淡地开花,散发着淡淡的香。
如若不是那股纯真自然的香气贯彻昼夜,供星伴日,人们几乎要忽略它了。
花儿们,素来喜好争奇斗艳,春风一吹,就纷纷使出看家的本事,树梢、枝头、路边、崖畔,好一番搔首弄姿、争奇斗艳。它们彼此“争斗”也就罢了,偏偏谢幕时还要捎带着拉扯个“垫背”的。比如,开着开着,突然发难,“踹”下去一两朵枝头正当红的花儿在风中凌乱……于是,枝头上才闹闹嚷嚷,姹紫嫣红,转眼间就落英缤纷,零落入尘……即便如此,它们总“集体嘲笑”那素净的槐花儿,笑她迟钝、迂腐,没有一丁点儿看风向、辨时机的眼力见儿,不能与春风共舞,更没有馥郁盈人之味!
槐花“听了”这些风言风语或花言巧语,均“无暇理会”,只是淡淡地、淡淡地、真真切切地开花。她“站在”妖娆的春风之外,迎着“夏天的威风”,“一树一树”,干干净净地开着,明明白白地香着。
槐花的美,岂是等闲人识得呢?
花期迟,但并非无用之辈。槐花儿,花蕊之甜,勤劳的蜜蜂知晓;果腹之功,饥寒的人记得。每一个洗手做羹的巧妇知道,将槐花儿洗干净,伴着面粉,搁锅上蒸熟,出锅的“麦饭”,依然清清白白不改本色,每一个品味槐花“麦饭”的人,都记得那股真诚的甜香,那股怡人的纯美。
如此妥帖白俊的槐花儿,着实也是有脾性的,你若敬她、爱她,她便清清白白地来,清清白白地去,留给你一个清清白白的美好印记,让你想起那美如珠串、形如细米、香如茉莉的一生之醉。无论如何,你可不要把它惹急了,她惹急了,敢于在天地间竖起铿锵宣言,瞬间,刺啦啦冲出绿色的仪仗队,噼里啪啦连珠炮一样炸开,千树万树,天地茫茫,犹如皑皑重孝……这纯粹的白,让你凛然,让你泪目!这一份纯白,映照了绿,映照了蓝,映照了污淖,映照了灰尘,也映照了辽阔天地,纷纷荣枯……
哦,槐花儿非俗物。她是带着哲思来世间行走历练的,它以单纯之力,以默然之态,以决然之境,告诉天地,告诉知音,也告诉熙熙路人:彼花开,此花开,花开花落花满天,唯有天地映晴空。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不说。
悠悠之境无边无垠,从此,余再不以小小格局去度量一朵花的沉默与素净,不再伙同周遭人一起围观槐花、揣度槐花,任由它以纯白倒映众相,以纯白还原纯白。
纯,白,乃天地之大美!

 秦锦屏 剧作家、一级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哈尔滨师范大学音乐学院(戏剧系)客座教授、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特聘剧作家、政府“首届杰出人才奖”获得者,著有小说、散文、话剧等作品。她参与编导的多部作品在中央电视台、中央广播电台等媒体播出,有十四篇散文、诗歌入选部分省市语文辅导教材,另有多部小说、散文翻译成俄、日文等。
秦锦屏 剧作家、一级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哈尔滨师范大学音乐学院(戏剧系)客座教授、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特聘剧作家、政府“首届杰出人才奖”获得者,著有小说、散文、话剧等作品。她参与编导的多部作品在中央电视台、中央广播电台等媒体播出,有十四篇散文、诗歌入选部分省市语文辅导教材,另有多部小说、散文翻译成俄、日文等。
